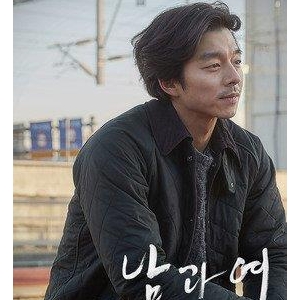我这一生至今,我觉得大抵还是顺遂的,除了在某些事情上。但人又怎能过分贪心。翻开历史,滚滚浪花翻涌过,留下的那些名字,又有哪一个这一生之中没有一件憾事呢。除了那个骑着青牛出函谷、一生缥缈无踪影,最后只留给世人“清净无为”四字的神秘老头,又有谁真的能不对命运报一声叹息呢。或大或小罢了。
早年的时候很喜欢苏轼,觉得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须发翁着实可爱有趣,诗句之中有着一种我行我素的豁达以及些许对岁月的藐视。稍长之后,对其生平略有了解。于是知道这首《定风波》作于其被贬黄州的第三年。此时的东坡,从乌台诗案中死里逃生,在黄州艰难营生,却视挫折于无物,俨然有种“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之感,风采令人神往。而后却又读到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句,又唏嘘不已,从此知道苏仙这一生,对命运亦有耿耿之处。
初识梅尧臣是在苏轼的那篇《上梅直讲书》里面,但其时,对梅尧臣并没有太多了解。其后,在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中,始知其生平。文章中欧阳修提到,当时梅尧臣已经名满天下,“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自己也是对梅尧臣的诗文推崇备至,“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但梅尧臣自己却“困于州县凡十馀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可谓是郁郁不得志,只能将其一生抱负寄托于山水之中。嘉祐元年,梅尧臣得到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举荐,回京任国子监直讲,仕途稍稍有好转,但是仍旧“位不过五品”。嘉佑五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又任参知政事,正式拜相,而那个被欧阳修推崇备至、世人其后以欧梅并称的梅直讲,苏轼笔下那个“不怨天、不尤人”的敦厚长者,却不幸死在了那年汴京的疫病之中。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李贺的这首《南园十三首·其五》,少年时候读来是那么的荡气回肠,豪迈无双。一直以为李贺应该是看过边关风雪的,或许和李白一样都是个放荡不羁的游侠儿,要不然胸中这豪迈之气那得如此勃郁。但是当我们翻开李贺的生平,却发现这位唐朝最好的诗人之一、诗中鬼才、文中翘楚,却因为小人妒忌,放出流言称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犯“嫌名”,终身不得考取进士,莫名的悲哀便涌上心头。再看“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时,那些看似豪迈的文字,分明句句都是李贺泣血为墨写就。毕生所学,却成为负累。命运啊,呵。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苏东坡没有遭遇乌台诗案,一辈子顺风顺水,这一生又会有什么变化吗。或许,宋帝王多了一位股肱之臣,但是,神宗皇帝已经有王荆公了,又何需再多一个苏国公呢。虽然封妻荫子是那个时代文人的毕生追求,但星汉璀璨,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又哪有苏东坡三个字,来得骄傲。
生命总不会沿着我们想要的方向给我们期待中的答案,不过生命,它又总会以另一种形式绽放,如苏轼,如梅尧臣,如李贺,如其他千千万万和命运不断较真的人。
最先知道蔡崇达这个人是很多年前一本叫《皮囊》的散文集。粗粗读过,说不上特别喜欢,但是文中朴实平淡却又略近哲理的话语,也给我留下了一些印象。这次的《命运》大抵还是沿袭了早前《皮囊》的风格,但是文字功力却又见长。许多落笔处,当时读来淡淡然有归有光之风,令人惊喜。其中太婆对于自己一生坎坷的命运,选择了不抱怨,始终以自己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最终打破命运诅咒。一切似乎不完美,却又那么的恰到好处,令人不住唏嘘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