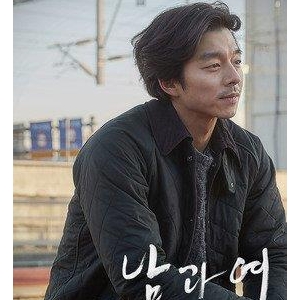旷新年
打开《鹅公坪》一书,熟悉的乡村景象扑面而来,尤其是特殊地方色彩的方言乡音,诸如半边户(夫妻一方农村户口、一方非农户口)、老虫(老虎)、把戏、堂客、伢叽(伢仔)、婶叽(婶婶)、打流(流浪)、双抢(抢收抢插)、牛栏、师公(巫师)、回来冇,妈得了(怎么得了),苦日子(三年困难时期)、划得来、贼牯子(小偷)、大水牯、打飞脚、泥巴路(没有硬化的乡村道路),乌龟车(轿车)、吃国家粮(吃商品粮)、打抱箍子(摔跤)、雷打火烧、水火无情、冇得饭吃了(没有饭吃了)、喂不熟的狗,还有“黄牛角,水牛角,各自各”这样音调简单,没有实际意义,却意味无穷的童谣。那种特殊的地方色彩与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乡村记忆好像突然打开了我记忆的阀门。
我与雄前兄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考上大学,离开农村,农村的记忆几乎完全重叠。我们是小老乡,雄前兄双峰人,我湘乡人。双峰属于老湘乡,1951年才从湘乡分离出来,独立建县。雄前兄书中的许多人物及其活动范围与我的故乡有许多交集或密切联系。杨家滩和桥头河是雄前兄叙述的重要线索,也是我童年时代许多故事传说的重要经纬。1975年开挖的恩口煤矿是离家乡很近的一座中型煤矿,家乡农民脱离农村最主要的出路也是当煤炭工人,不少乡邻是恩口煤矿的工人。我的家乡壶天镇磨石头的红土地是画家罗尔纯作品色彩的源头。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个人生活在什么环境,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鹅公坪》描绘了一个个富有传统农村特点的农民,例如,人生记忆的第一个起点的父亲的干娘六奶奶,“小脚,黑帽,沟壑纵横的笑脸,满布疙瘩的拐杖”。他最亲密的童年伙伴的母亲春婶叽,额头上长着肉球被人戏称为“气球老公”的细公公,苦命女人妙玉姐,做法事的巫师赞师公,算命先生罗富生,看水人春初老倌,这一个个异常鲜活、性格与命运各异的人物,烘托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生活图景。那个时代的生活充满了艰辛、苦难,同时也不乏温情、道义。尽管充满各种各样的灾难与变故;然而,那时的农村仍然是一个平静、稳定的传统社会,典型的费孝通所谓的“熟人社会”,过着简单朴素、相对健全的伦理生活。他们坚韧倔强、淳朴善良,知足常乐、相互信任,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可以相互托付,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你来我往,相互帮衬,充满世俗温情与历久弥新的人情。对于我们这些从农村中学考上大学的农村孩子来说,永远无法忘怀无私地哺育了我们的乡村教师。那个时代的师生关系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最无私、最高尚、最纯粹、最美好的一种关系,其纯度甚至超过了父母与子女之间血缘的关系。就像小学老师刘新乾老师所说的:“不管你穿花衣服还是穿补丁裤,不管你家有做官的爹还是有讨米的娘,只要在我班上,我都把你们看成好学生。”
有一个仅仅只属于湘乡人这个特殊的群体的方言词汇引起了雄前兄浓厚的兴趣与持久的关注。这个词就是“含糖”。含糖这个词不仅外乡人永远都不会懂,而且即使湘乡人自己也已经不明就里。它是湘乡人特殊的历史记忆的沉淀,是湘乡人特属的光荣与梦想。雄前兄对这个词情有独钟,着意发掘,发出了深刻的灵魂之问。他在《含糖岁月》里写道:“小时候,鹅公坪从来没有‘曾经’‘从前’这样的词汇,只要是讲过去的事,开口第一句就是‘含糖’。从 16 岁离开故乡开始,每年都回家探亲,每年都听到含糖,听到含糖一词心里就咯噔一声,想这是一个什么鬼。一直到 2020 年,我才破解‘含糖’这个心心念念缠绕多年的谜团。”雄前兄由阳剑先生主编的《双峰方言之东扯西绊》中“咸同”的词条推定含糖就是咸同:“一个仅流行于湘中地区的方言词汇。它是清朝咸丰、同治两个年号的合称。历史上有‘咸同中兴’之说,在双峰及周围县市中,‘咸同’表示‘过去、曾经’的意思。咸丰同治年间,由于曾国藩和湘军的崛起,湘乡人文蔚起,名动全国。湘乡人总督巡抚以上的封疆大吏比比皆是,至于四品五品官员,则不足为奇。同时,由于湘军官兵通过战争积累了一部分财富,地方经济十分发达。因此,这段辉煌的历史,后来人说起时,就十分自豪,总是说:“咸同年间,我们这儿如何如何。久而久之,就演变成‘咸同’,表示‘曾经、过去’的意思了。 可以断定,‘咸同’这个方言诞生最早在光绪年间,离今不过一百多年。”含糖这一个极为特别的方言词其实就是一部高度浓缩的湘乡地方史与文化史。湘乡的自豪与辛酸、辉煌与沦落,尽在其中。咸同之后,湘乡从历史的高峰跌落,重新沦入庸常暗淡的日常生活,辉煌不再。雄前兄一语道破:“咸同到含糖的语义演变,我觉得大有深意。几百万湘乡人在大概 160 年的历史中,硬生生将‘过去’‘曾经’‘从前’这些词汇挤出去,用‘咸同’ 替代,这要有多么强大的文化信念和凝聚力!而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咸同的文化竟然变成含糖的味觉,对湘乡人来讲实在是从天堂跌入地狱的感受。” 我们家乡的发音略有不同,经常“要是咸阳啊”,“说起咸阳啊”连用,带有强烈的返古的味道,充满对过去的好时光的无限怀念和盛时不再的无尽感慨。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劫掠、蹂躏了包括最富庶的江南在内的大半个中国,最后曾国藩率领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同时发动了成为中国现代化起源的洋务运动,使古老的中国第一次睁眼看世界,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同治中兴,并且因此将从来都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湖南人带上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大舞台。咸同是湖南人的高光时刻,更是湘乡人的高光时刻。此前,湖南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默默无闻,“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 “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湖南长期处于中华文明的外围,直到中华文明的重要高峰北宋,湘乡仍然是中原文明的边疆与文明分界线。湘乡往西便是化外之地,相邻的安化以及新化和怀化等地名都是北宋熙宁年间朝廷镇压南江蛮和梅山蛮后的赐予,它们是王化、归化、教化之新地。在明末天崩地解的剧变中,湖南诞生了著名的学者与思想家王夫之,他既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总结,也是传统思想学术的批判与超越。王夫之的思想学术埋藏、蛰伏了两百年,经由曾国藩和湘军,得以广泛传播,发扬光大,驾顾黄而上,成为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从周敦颐到王夫之到曾国藩,湖湘学脉,不绝如缕。19世纪,中华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四塞之地的湖南,长期沉潜的思想学术与野蛮的血性在大危机中释放出了空前的能量与耀眼的光芒,似乎几千年的沉寂就等待着这一刻的爆发。以经世致用为基本特点的湖湘学派由湘军而震动天下,光耀世界。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第二年,曾国藩以丁忧身份奉旨创办地方团练,以同乡、同族、师生、亲戚为纽带,组织起一支呼吸与共、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的强大军队。湘军之所以有着巨大的凝聚力、生命力与战斗力,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根本在于,湖湘学派构造了湘军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脉。这是一支有思想、有学术、有信念的军队。他们形成了一个文化与命运的共同体,无论湘军各部之间平日有着怎样的矛盾与利益冲突,但在危难时刻,都会顾全大局,倾力相救,生死与之。全部湖南人与湘军荣辱与共,凝聚成为一个紧密的文化利益共同体,群星璀璨,人才井喷。湘军对湖南人而言,不只是一支军队,更是一种文化信念。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危急时刻,湖南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改变了民族命运的历史人物。几乎人尽皆知的杨度著名的《湖南少年歌》充分体现了近代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慷慨激昂,气势磅礴,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壮丽的篇章。1910年,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到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抄写了日本著名维新政治家西乡隆盛(实际上是日本和尚月性原作)的一首诗留别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它体现了近代湖南人胸怀天下,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
湘军的功业给湖南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无上的荣耀与充分的自信,尤其是湘乡人长期陶醉与沉浸于这种往昔荣光。我们家乡对于财富的终极想象就是,打开南京发洋财。中国最富庶的江南积累了两百年的财富为湖南在近代的崛起与发达奠定了物质基础。即使这种荣光早已褪色,生存的高地早已沦陷,他们依然相信自己的家乡是世界与宇宙的中心,标志着人类财富、文明与幸福的顶峰。全世界哪里最幸福?当然是中国人民最幸福。中国哪里最幸福?湖南。湖南哪里人最幸福?肯定是鹅公坪。湘乡人这种对家乡幸福的执念如此熟悉、如此同质化,完全可以将鹅公坪换成我的家乡壶天。1980年,当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乡到长江边上的一座大城市去上大学的时候,我的父母、乡亲曾经为我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过一种未知的生活而忧虑,他们最担心的是我能否忍受与适应异乡野蛮人的食物,他们基本上认为,我家乡以外的其他地方都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尽管除了咸同流水一般的金钱与富足,我们家乡的农民几乎一代又一代都在重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但是,他们依然信心满满地觉得只有自己家乡的生活才是世界上最合理、最完美、最幸福的生活。作为农民最大特点的安土重迁是农业文明自然生存状态的反映。游牧民族与商业民族那种离乡背井、人在旅途的生活被农业文明视为最大的不幸,是万不得已的生存下策。不论是老大嫁作商人妇,还是昭君出塞,都被视为人生最大的灾难与不幸。农民安土重迁的自然生活的特点造成了他们的狭隘、短视、保守与孤陋寡闻。
湘乡由咸同一路跌落,我们出生的时候,已经跌入历史的谷底,贫困、苦难与绝望已经达于极点。“同样是霸蛮,左宗棠抬棺西征收复新疆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而妙玉、 鸿轩、富求和我哥的霸蛮,却是鸡零狗碎的求生;同样是耐烦,邓显鹤一生致力于湘学复兴事业,焚膏继晷为湖南士人打气加油,孜孜矻矻挽民风民俗强悍嚣张,而我少年时代乡亲的耐烦,无一不是一亩三分地的苦煎苦熬,无一不是三百六十五天的苟延残喘;同样是吃苦,二万五千里长征实在苦,但红星照耀着中国希望笼罩着大地,而我父亲的吃苦,是五十多岁老汉每天来回六十里路拖板车的苦,而且一拖就拖了差不多十年。永远不能责怪老百姓。错误的政策导致巨大的苦难和贫穷,在肚子都吃不饱的饥饿岁月,没有人仰望星空,也没有人敬畏心中的道德准则。‘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道德人格消失了,假大空和欺瞒骗成了常态,民风就猥琐了,士气就崩塌了,有哪一个还想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如果说《爸爸爸》等新时期文学所谓“种的退化”是新启蒙主义理念化的表达的话;那么,对于在湘中丘陵这片狭小、贫瘠的土地上煎熬着的人来说,生存退化是一种残酷的现实。
农业文明和农民从根本上是狭隘、保守的。我们成长的时代,又是
本文来自【湖南日报】,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