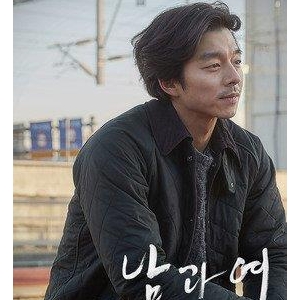一曲《惊梦》诉尽苍凉
——观话剧《惊梦》有感
作者:李 健
陈佩斯导演的话剧《惊梦》将故事场景设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原平州城。彼时国共两军鏖战正酣,昆曲戏班班主童孝璋带着和春社走江湖演出,刚进城就遇到两军对垒的拉锯战,戏班上下被困在战乱中生计无着、命悬一线。面对残酷战争和无处可走的困境,班主童孝璋与戏班众人在生存的夹缝中,苦心周旋,发生了一系列啼笑皆非、悲喜交加的故事。
《惊梦》在喜剧的笑料中,把小人物被历史洪流裹挟,在时代夹缝中挣扎求生的无奈与心酸,表现得真切自然,包含着深沉的人生况味。剧终时,伴随着漫天大雪,戏台上唱起清丽婉转的《牡丹亭》,将微茫的希望寓于苍凉之中,展现了艺术和人性的温暖亮光。
戏剧艺术通过矛盾冲突来推动情节和塑造舞台人物,喜剧更是借助误会误认、角色错位等手段使故事情节曲折多变、紧张激烈,来强化戏剧性,增强冲击力。纵观《惊梦》全剧,糅合了戏、人、战争三个方面的矛盾线索,使之相互映衬交织,在营造和化解冲突中将故事推向高潮。
“传戏”的坚守与“改戏”的冲突
和春社作为有着60年历史的昆曲大班,童孝璋遵循着“戏比天大”的古训,坚持凡事按规矩办,“应了的戏就得唱”。在排演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冲突:正宗科班的昆曲演员遇上新戏《白毛女》时,戏班文丑拒绝出演,坚持“师傅没教过的戏不唱”;童佩云质疑喜儿的穿戴行头不合规矩,拒绝穿现代戏中的工农服装,这种冲突是昆曲《牡丹亭》和歌剧《白毛女》在艺术形式上的反差,因为在演员们看来,昆曲班演一出像梆子的《白毛女》是对传统的背叛。
当童佩云和何凤岐用曲调婉转的昆曲唱腔来念《白毛女》中喜儿、大春的说白,当一众想当然的戏班演员推出“白娘子”扮相的喜儿、“赵子龙”扮相的大春亮相时,产生了强烈的违和感,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这种反差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艺术形式的违和感,反映了和春社那种封闭的戏剧传统与当下老百姓水深火热的生存现实相脱节,所产生的强烈反差。
这种强烈的反差,被巧妙地从戏班内部化解了。乐师邵伍看了《白毛女》剧本后深受触动,“杨白劳卖女抵债、喝盐卤自杀”的悲惨遭遇,让他想起了父亲和自己的命运,产生了与剧中人物命运与共的强烈共情。此时,战乱的时局已经容不下一个视戏如命的昆曲戏班,涌动着激烈社会矛盾的苦难现实,也迫切需要唤醒民众的艺术力量。于是,戏班从为了生计被动排演《白毛女》,转换为从内心感受中贴近《白毛女》。戏班的前后反差和转变,与其说是昆曲《牡丹亭》和歌剧《白毛女》两种艺术形式的冲突,不如说是戏班开始了从“为艺术而艺术”到“为人生而艺术”的初步转变,使之从单纯地专注于打磨“一出戏”,到逐渐在戏中关注“一个人”的命运。
戏梦人生的痴迷与执着
《牡丹亭》是体现汤显祖“至情论”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戏曲史上最负盛名的浪漫主义杰作。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一往情深,穿越生死,渗透着追求个人幸福、呼唤个性解放的人生理想。在和春社,扮演杜丽娘的童佩云和扮演柳梦梅的何凤岐从小一起唱戏、对戏,因戏生情,许下要一起演一辈子戏的诺言。然而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时局之下,他们的爱情除了生存的困境,还要经受着生死的考验。先是何凤岐的父亲何广顺瞒着他们,暗中骗何凤岐出城投奔香港经商的叔叔;再是何凤岐拿着解放军的路条出城,被国民党军当作奸细。这些坎坷磨砺,让他们在逆境中释放了压抑的情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内心爱情的力量。至此,童佩云、何凤岐经由《牡丹亭》的剧情和战乱离合的坎坷现实,在戏里戏外实现了“至情”的呼应。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和春社稀里糊涂却出色地完成了《白毛女》的演出任务,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军的士气。当再度进城的国民党军让戏班演一出放松身心、提振军心的戏时,戏班便天真地演了《白毛女》。戏还没演完,导致“两个营的士兵开了小差”,实打实地来了一场“赤化宣传”。就在何凤岐险些被国民党情报处长处决之际,童佩云、何凤岐毫无畏惧地唱起《牡丹亭·惊梦》中的【山桃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在生死绝境下,他们无视敌人的枪口,互诉衷肠,置生死于度外,用这首真挚、唯美的定情之曲,令士兵将行刑命令忘却脑后。此时,话剧《惊梦》通过和春社在国共军营中两次演出《白毛女》,尽管过程截然不同,结局却又异曲同工,都焕发起对于“人性”发现和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童孝璋和戏班众人,实现了认知的成长。童孝璋从只顾着老规矩,只知戏文中的忠孝节义,不懂现实中的家国大义,通过一系列误解、冲突、矛盾和两次演出《白毛女》的过程,逐渐转变了狭隘的认识,从而更加朴素地认同共产党和秦司令所讲的“自己一个人过舒服日子不行,得让天下的百姓都过上舒服日子”的道理。由此,戏班从“为艺术而艺术”到“为人生而艺术”的深层次转变,实现了从“戏”到“人”的又一次升华。
戏里戏外的梦中苍凉
战争是残酷的,一般而言喜剧较少涉及战争题材。话剧《惊梦》却把故事置于一个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战局之中。全剧以常家祠堂的戏台为中心,通过戏台的转角、分合、移动,来交替切换战争场景和日常场景,穿插着演绎《牡丹亭》《白毛女》的故事,交织叠加起戏里戏外、戏中有戏的笑中带泪的命运叠奏曲。
在战乱年代,戏班众人和城中百姓一样,是被时代裹挟的卑微个体,难以掌握自我的命运。剧中有一个细节,解放军文工团女兵被杜丽娘的扮相深深吸引,希望能够向童佩云学戏,然而转瞬之间战争就吞噬了她年轻的生命。随后,解放军宣传科长牺牲,秦司令重伤,国民党战区司令谭世杰在山穷水尽之下自杀……战争扭曲了生活的日常,无论是军官、士兵、百姓,他们的个体需求被剥夺,这无疑是乱世纷纭之下,个体命运的悲哀。
最终,和春社为所有亡灵演出《牡丹亭》,在漫天大雪中,一曲真正的昆曲抚慰所有故去的亡魂,用艺术抚平战乱时局所带来的伤痛,焕发起对人性的发现。这是全剧最写意惊艳的手笔,既是对全剧“戏中戏”故事架构的一个收束,更是对人性、对生命的尊重。至此,话剧《惊梦》以博大的胸襟和创作格局,增强了艺术表现的主题,展现了超越生死的人性光辉。(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