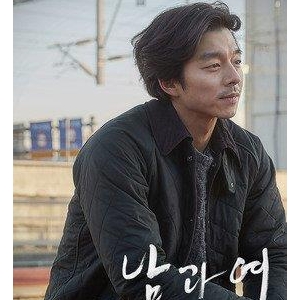《天意》是一部由阿伦·雷乃执导,德克·博加德 / 艾伦·伯斯汀 / 约翰·吉尔古德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天意》观后感(一):语言实验与家族史
要想获得对不可名状的事物的表述就要体验未知的情感,而这种试验必须跟自己情感羁绊的最紧密的家人进行才能获得最好的效果,而试验的后果是连锁式和持续性的,能影响至一代或数代,家族中的情感基因就这样被有意识的改写,并像物理实验中记录数据那样被作家记录在自己的小说中。作家最后敬自己的子女“敬你们所有人的未来,你们的未来还未曾书写,不是吗?”即便到了最后时刻父亲还在矫饰自己对家族命运的独裁。到了晚年主导权不知不知觉就到了子女一边,逐渐丧失健康的他需要被爱,而他也明白子女们不可能真正爱他。最后那个没有告别的告别仪式就是这种复杂情感的体现。
《天意》观后感(二):《天意》 ——阿伦·雷乃同名影片短影评
《天意》
——阿伦·雷乃同名影片短影评
巾城/文
可以把影片里作家的幻想部分理解为摘掉面具后的现实。他的潜意识的不安让他看到了那些和他至亲的人相互间不可被削去的隔阂,这其中有成长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的原因。
影片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配角(几乎每一个有台词的角色都承担相当比重的戏份),社会环境本身的疏离感完全靠角色间的关系及台词和布景急剧的转换制造。这种设计把每个人心中的恐惧和其带有潜意识成分的行为放大到极致。在观者看来,很多举动或它们之间的接续是荒谬的,但通过布景(常带有明显的人工痕迹)、意象(最显著的即酒杯和酒)和台词(“一种严谨和逻辑的语言”——这句话本身即带有很强的反讽性质)的重复及发展,这种荒谬渐渐变成了一种必然,仿佛影片中所有发生的悲剧是真的,而我们生活的世界却是这种真相被盖了一层幕布之后的虚饰。
影片的最后,当一切回归现实,角色身上可以清楚感觉到一种带棱角的掩饰、一种被修复的温情,这时贯穿全片的白葡萄酒突然变成了红酒,在父亲的要求下,角色们制造了片子最后真正意义上抒情的几个镜头。这是一种孤独,在阿伦•雷乃的许多电影里我们都看到这种束手无策的孤独。也许在所有对“糟糕的世界”的充满学院气息的描述之后,这是大导演留给这个世界最终的结论。
《天意》观后感(三):【参考资料】一位外国影评家的评价
rovidence (1977), written by David Mercer and directed by Alain Resnais, is an extraordinary film. It’s the only movie Resnais ever made in English. It’s basically a cast of five: Dirk Bogarde, David Warner, John Gielgud, Ellen Burstyn and Elaine Stritch. What’s so amazing about it is that you don’t realize until the end that the story you’re witnessing is the rabid dream of a writer. The protagonists are always changing scenes but it’s not in any way faux-real. They walk down a long flight of stairs to enter a room and the next minute they might walk into the same room – without the stairs – and you realize Resnais has accommodated the slight adjustments of memory and fantasy. It was shot in France but Resnais sent an additional camera crew to America, so the film switches very subtly between the footage shot between the two locations, which creates an unhinging sense of non-location.
该片中,有句台词,我很喜欢:“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一个建筑物,根据你的心意造成的。”
《天意》观后感(四):《天意》:创作的真相
作为法国电影新浪潮左岸派的代表导演,阿伦·雷乃向来长于文本的解构,并且能够将极富文学性的文本内容通过带有实验性质的视听语言外化出来,将文学和电影两种媒介紧密贴合,带给人亦真亦幻、虚实叠加的暧昧观感。本片同样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影片的叙述口吻具有极强的文学性,讲述的又恰好是一个小说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故事,两层文本就这样互为表里,把创作的本质和真相解说得异常通透。 在这个故事里,雷乃无非讲述了一个核心命题,即创作永远代表着一种对于自身的回顾。而且在这回顾的反复动作和持久过程中,一定有一个人或一件事长久地伫立在遥远的记忆深处,让心为之隐隐作痛,想忘不能忘,成为一切矛盾的触发点,成为最疼痛、最深切的刺激。在此基础上,创作者才会为了遗忘,或曰更加隐秘的铭记,而不断出于辩解的目的做出忏悔的姿态,继而构想出一个在伤痛中不断经过历练和美化而最终成形的理想形象,直到把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投射成某一阶段或某个截面中的自己,这就是文学创作的内在逻辑。这个故事理解起来着实复杂、凌乱,但最终的意义呈现也着实犀利、精准。 在影片中,雷乃选择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来直观地展现创作者在角色上的心理自我投射。他让小说中的角色们不断地进行身份嫁接,一边在人物之间构成更丰富的联系,一边深化作为创作者的父亲难以摆脱的执念——逝去的妻子,莫莉。在小说中,起初,克洛德是因母亲莫莉的死而憎恨父亲的独子,后来,这一憎恨父亲的身份由被指认为独生子的伍德福德暂时接替;起初,克洛德的情人海伦只是被形容为“像他的母亲,莫莉”,渐渐地,她的身份开始向上层僭越,终于在和转化后的伍德福德的交流中彻底变成了母亲莫莉。再如,起初,是尚未被指认的伍德福德枪杀了逃窜丛林的作者本人,在小说的结局,同样的情节再次发生,射杀的双方却不同了。这一次,曾经杀了人的伍德福德浑身长毛,又从私生子变成了父亲的化身,成为被射杀的对象,而曾经在法庭中厉声谴责枪杀行为的克洛德则成为了凶手,这时候,他重新回归了那个怨恨父亲的儿子形象。这一次的枪杀才算是完成了作者眼里真正意义上的弑父。这一类身份的连环嫁接在影片中随时发生,时常让人猝不及防,陷入混乱。然而这份混乱与小说之外创作者不断酗酒、自我放逐的颓废相得益彰,反而衍生出一股迷人的朦胧气韵。此外,追溯到身份嫁接的最初环节,我们也会发现,作者其实早已经从各个方面打破了真实世界的伦理设定,让作为母亲替代品的海伦成为大儿子的情妇,又让作为私生子的伍德福德变作大儿媳的情人,这大概也暗合了文学创作的去道德性及其尺度的自由。 如果说小说里故事的结构已经足够奇妙,那么再结合结尾处那段短暂的现实来看,整部影片的表意就更完整也更惊艳了。最后,当现实披露,我们看到作家的晚年生活和他在小说创作中的笔触大相径庭:他的笔触那样荒唐颓丧,他的生活看上去却是无比的光鲜快活。然而,在这幸福的天伦之乐背面,仍隐约可见裂隙的存在:克洛德对父亲的顺从带着卑微的隐忍,而父亲即使在面对儿子们的关怀时也不挑好听的话说,每每让孩子们面露难色。可以说,在这个看似完好的家庭里,母亲一人的缺席已然对家庭的每一个分子造成了隐性的伤害。父亲作为作家,选择把这份潜藏的不快投诸虚假的文学创作,用一种扭曲的方式纾解内心的阵痛。回到现实中重看,好像父亲才是整个故事里最“混蛋”的那个人,而在小说中,其他角色之所以显出或多或少的“恶”,也不过是因为他们被迫地沾染了创作者的原罪而已。但从创作的角度而言,创作者又确乎需要这样一种敏锐的质疑一切的眼光,正如父亲不相信大儿子对自己的恭顺,更不相信他们夫妻的恩爱。对于其他人而言,这也许会被视作阴暗的想法,但对于创作者而言,此番言论的罪责完全可以被开脱。因为,如果他没有这样一种幽暗的,独到的思考的本能,那么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又和真实有何区别?而如此这般风平浪静的真实和暗流汹涌的虚构相比,又谈何魅力呢? 在小说中,已然“成为”母亲的海伦和克洛德说的一句话颇有深意。她问克洛德,自己的到来是否在他的生活中造成了一场危机。显然,她是代表缺位的母亲出现在小说里,出现在小说中克洛德的生命里的。在现实中,父亲始终觉得母亲的缺失造成了克洛德对自己的疏远和冷漠,尽管雷乃对此不置可否。而在虚构的世界里,父亲安排母亲出现,却让她成为所有角色包括克洛德走向毁灭的导火索,我想,这是否也可以看作是父亲对自我的某种安慰呢?他把虚假写得越坏,现实就会被衬托得越好。 创作者或许是幸运的,他们可以把伤痛转化成崇高,把破败点缀成唯美;创作者同时也是不幸的,他们往往于创作的迷雾中走失,不可遏制地,一厢情愿地栖居在自己的想象编织成的圈套里。曾经我们羡慕、崇敬那些故事的创作者,这一次,雷乃却凌驾于其上,说穿了创作者心底的故事,揭晓了他们不为人知的残酷真相。 影片的结尾,孩子们在父亲冷言冷语的驱逐下一一离场,徒留他一人沉醉在生日的宴饮里,这大概也揭示了雷乃创作这部影片的根本意义,正在于让人们知晓,创作这回事尽管带着神圣的光辉,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它仍旧是一片危机丛生、不应随意涉足的禁区。
《天意》观后感(五):导演说
法国“新浪潮”中涌现出来的100多名年轻导演中,剪辑师出身的阿仑·雷乃实为佼佼者。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打着自己鲜明的印记,无一不是名副其实的“作者电影”。1959年拍出的《广岛之恋》,被誉为“当代文学杰作”。1961年推出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远非像某些影评家所预测:只能得到少数知识界影迷的青睐,它赢得了全世界观众的认同和推崇,公认为一部划时代的影片。雷乃的视野从未局限在马里昂巴德的那家巴洛克风格的豪华宾馆里,而是像后来拍出的《慕里耶》和《战争结束了》所展示的那样,他要以一种全新的电影语言,揭示人类社会更深层的现实。这位“左岸派”代表人物认为:传统电影的线性陈述法,只能反映“群体社会表面的现实”,人类深层的思想活动本来就是时空交错不合理性的意识流。有些后现代主义作家甚至强调:不用意识流手法描绘出的现实,只能是一种被人们按照自己意愿加工歪曲的假真实。在这部荣获7项恺撒奖的影片中,阿仑·雷乃确实成功地揭示了一位作家深层的思想活动,展示了一部文艺作品的诞生过程。
天才的阿仑·雷乃26岁时,就拍出了法国第一部艺术影片——《梵高》(1948)。这位电影艺术家的一大特点,是他始终和法国文学界的著名作家进行密切合作。他的第一部故事片《广岛之恋》,是当代独领风骚的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为他编写的剧本。第二部时代巨片《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剧作,又是新小说派代表人物阿仑·罗勃一格里叶的作品。《战争结束了》的编剧又是文学界颇有名气的乔治·桑波伦。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阿仑·雷乃聪慧过人才华超群,为什么总是请他人捉刀,而自己不搞独立创作呢?这个问题直到《天命》这部影片问世时,才得到答案。
《天命》无疑是阿仑·雷乃一部十分成功的代表作。这部影片的特点之一,是导演和编剧建立了世界史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关系——新型的编导合作方式。大家知道,法国的编剧过程和过去美国好莱坞式截然不同,美国的制片人是影片的核心,编剧根据导演意图对一个现成的剧本进行结构,为对话进行加工润色。在欧洲,导演历来是主宰一切的。但事实上,这往往只是影片开拍后的情况。在此之前,导演往往不得不去求助于作家,或者自己和一名职业编剧共同去改编一部名著。像特吕弗那样借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的并不畅销的小说,来表达自己情感世界的观点(如《朱尔和吉姆》),实为凤毛麟角。当然也有像玛格丽特·杜拉或者阿仑·罗勃-格里叶这样的作家,既写小说也进行电影剧本创作。愿意把这些文坛巨子的作品搬上银幕的导演自然不乏其人。因此,在欧洲历来是电影艺术家为文学家服务,导演为编剧服务。即使像雷诺阿这样的大导演,电影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自然无需赘述,但他影片所表达的思想,传达给观众的哲理,仍然是诗人兼编剧普莱维或斯派克的。鼎鼎大名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德·西卡,他拍出的几部影片,已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事实上,他是忠实地按照著名编剧柴伐梯尼为他写成的分镜头剧本拍摄、剪接而成的。功劳自然是大家的,但究竟谁才是影片的真正主人呢?多数人想到的是柴伐梯尼。因为影片的结构、对话和拍摄细节,都是编剧的思想。导演在选择演员(往往是非职业演员)、拍摄角度和影片节奏处理上,完全执行了柴伐梯尼的意愿。
阿仑·雷乃在拍摄《天命》的过程中,与编剧达维·麦塞的关系是:编剧不折不扣地为导演服务,也可以说是文学为电影服务。1975年夏天,阿仑·雷乃告诉达维·麦塞,他想把一个艺术家构思一部作品的过程拍成电影,着重要表现艺术家创作时深层的意识活动,麦塞建议以贝多芬创作《月光奏鸣曲》的过程为背景,很快就交给雷乃一个剧情梗概。雷乃说,第一我不要19世纪的人,第二我对剧中的外部事件毫无兴趣。我要把主人公关在一间房子里,让他胡思乱想,我的兴趣就在于表现他那些不着边际不合理性的意识和他的原始冲动。麦塞又写了一个画家和一个雕刻家如何见景生情的故事。雷乃把它们都锁进了抽屉。最后,雷乃指示麦塞去写一个小说家的故事。1976年冬,导演和编剧一起七易其稿,麦塞写出了文学本,雷乃在文学本上注明了分镜头的处理意见。开拍以后,麦塞一直不离阿仑·雷乃左右,随时对结构和对白,按照雷乃一些即兴的思路,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在后期剪接过程中,麦塞也尽其所能地满足了导演的要求。两个人自始至终的默契合作完成了这部“诗意现实”的思考片。应该说,《天命》完全是雷乃的个人作品,他达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一部真正的“作者电影”诞生了。
评论界有人说:“《天命》与其说是一部电影作品,毋宁说是一部银幕上的文学作品。”阿仑·雷乃巧妙地潜入了一位年事已高但笔耕不辍的作家的心灵深处,进入到他和构思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之间,窥探了他们最隐秘的内心世界。老作家克里夫在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里,不断忍受着身体和心灵的苦痛,构思着他的小说。书中的角色无一不是他的亲人:儿媳、儿子、妻子、私生子和儿子的情人。他让这些人互相撕打、冲撞、仇视、爱恋,借以发泄他的心中最真实的情感。老作家的心血来潮或者潜意识的某种冲动,造成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这部影片以生日宴会为界,通过强烈的明暗光线对比和逼真的音响效果,把作家构思的故事与外界真实,分为分量不等的前后两部分。影片绝大部分表现的是克里夫的创作灵感、梦幻、个人回忆、幻觉和他的构思脉络,结尾部分才是现实。两个不同的视点形成鲜明对照。前一部分是作家下意识的自由联想和在理性指导下的创作过程。这两条心理动作线不断交织穿插,同时也互相呼应对比。反复出现的“套层段落”表现了作家的创作困惑、心理矛盾和感情困惑。例如柯文没头没脑闯进正在洗澡的海伦房间时,克里夫把他赶走了。当克罗德和海伦像做梦一样脱掉衣服,柯文的弟弟又跑进来,并把自己关在浴室里面。克罗德和海伦对这个人的出入像没看见一样,而下一个镜头这对情人又出现在另一间摆设全然不同的房间里。观众会意识到,上一场戏失败了,作家进行了修改。这些都说明了有意识的文学创作来源于无意识或下意识的感情纠葛的痕迹复苏。这些不合理性的构思在文学创作中虽是败笔,却给影片增添了不少真实感。
作家的创作主线,交待了克罗德和同父异母兄弟柯文之间厌恶仇杀的由来和索尼娅对丈夫由不满到不忠,直至反目成仇的过程。克罗德对父亲不满、仇恨、咒他早死的原因,我们从克里夫的往事回忆中找到了答案。按照弗洛伊德理论,孩子对父母的成见,必须追溯到他童年的遭遇。
影片到宴会结束时打住了,但老作家的创作并未到此中止,他又举起了酒杯,一个新的不眠之夜马上又要到来,无穷无尽的思绪和幻梦又将接踵而来,当然,他的小说也将进入一个新的篇章。
《天意》观后感(六):语言的迷宫
雷乃是以电影语言的先锋试探而出名的。通过精巧的结构和错落的时空安排,把叙事隐藏在语言的迷宫里。《天意》也许是其中比较容易解读的一部,但是却是我非常欣赏的一部。
《天意》的故事表面看来很简单,不过是这个作家构想中一个关于四角恋情的小说,但是却在主人公潜意识的神出鬼没下刀工斧凿成为对他个人过往的梳理和对的剖析。
小说里那个不靠谱的四角恋情其实不过是:妻子爱上被告,律师丈夫会了旧情人,嫉妒的丈夫杀死了情夫。小说后面的故事却没有那么简单:父亲的冷漠造成了母亲的自杀,童年不幸的儿子与父亲产生了不可弥合的隔阂,最后完成了“弑父”。当然,这只是摆不上台面的潜意识,对应的现实版故事可是光明得多:亲生儿子拥有美满的婚姻,私生子融入家庭,作家父亲写出了本新小说。
小说里的两个男主人公,在作家克利夫的自觉和不自觉中成为他两个儿子,这不仅以相同的名字、相同的演员来“明示”,甚至可以直接从文本中得出。电影在叙述时,旁白的克利夫总是脱口而出将小说里的克洛德喊成“我的儿子”。
死亡是萦绕着这个小说的主题,因为克利夫离死亡这么近。片头出现的濒死的狼人就是克利夫自己——在艾丁顿解剖狼人时,克利夫的旁白说道“哦,他准备划开我的身体!”显然,他把自己带入那个奄奄一息、病入膏肓、快要变成狼人的老人。而长得像他死去妻子莫莉的儿子情妇海伦,一出场就宣告“我快死了”。城市里有大批的人即将变成狼人,即将死去。死亡的气息弥漫着整个城市,弥漫着整部小说,其实也就是弥漫着他那颗恐惧的心。
正因为对于死亡的恐惧,他才流露出对生的向往,对“结实的肌肉、柔软的皮肤”,对人体美的留恋,对美酒所象征的健康人特有的享乐的执着。他通过克洛德的抱怨,道出对自己状况的憎恨:“你是一个亿万富翁(或者以克利夫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当然也是有钱人),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丧失尊严的方式苟延残喘?!你可以大喊大叫、酗酒、骂骂咧咧地走上黄泉路,人们也许惊讶,但是还能怀着包容心袖手旁观……”事实上这暗示着他的现实处境,他就是在用咒骂和酗酒度过他病痛而尴尬的老年。衰老和病弱是这样一种剥夺人的尊严的窘境,他不得不在写作中停顿下来,愤怒地抱怨肮脏的短裤。它让一个骄傲的男人如此狼狈,以至于他宣泄着对自己的不满。
也正是因为死亡的威胁和老年的孤独感,他对儿子们的态度十分敏感。尽管我们在片尾看到,两个儿子对他十分恭敬顺从,尤其是克洛德,但是克利夫眼里看到的他们并非如此。大儿子因为母亲的死,不可能与他亲近(至少在他想来是如此),小儿子是个后来承认的私生子,总似有些距离。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小说中两个儿子性格的设定。小儿子扮演的伍德福德则体现出柔软的同情心、美好的诗意、与世俗的疏离感,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对死亡的亲近感”。不同于现实生活中大儿子的内向和顺从,在幻想里,克洛德理性、冷漠、富于攻击性。我们可以尝试着不去将他们一一对号入座,那么伍德福德和克洛德是否可以看作是儿子们的现实态和在幻想态中的区别,甚至包含着克利夫自身的部分人格?伍德福德的诗意和克洛德的冷漠、尖锐,并存在这个复杂的老人身。
在克利夫的回忆里,出现了对记忆的分裂的态度:一方面留恋美好的时光,如“海边的阳光,凉爽的葡萄酒,晒得庄重的肤色”,以及笑着对他说“你有你的魅力”的妻子;另一方面,因为对于妻子自杀他所感到的痛苦是如此强烈,他所感到的负疚是如此深埋于心底无法见到阳光,因而他始终在抗拒回忆、拒绝忏悔,但是最终还是服从于内心强烈的愧疚感。
没错,老爷子的心结就是妻子的死亡。在他的梦魇里,他不止一次地假人物之口对此事作出辩解。法庭上的庭辩,伍德福德在回应律师克洛德的步步紧逼和道德审问时说:“我觉得人们有权利选择死亡的理由。”这可以看作是为他自己所作的辩护。克利夫甚至让小说里的伍德福德在广场上贴出横幅:“人们应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而克利夫和妻子的关系也通过克洛德和索尼娅的关系折射出来。因为我们能看到现实中克洛德和索尼娅是非常融洽的一对夫妻,而小说中他们的生活却是平淡至剑拔弩张。克利夫假克洛德之口说,他们的婚姻“处于一种无法言说的倦怠情绪中,我们沉默地呐喊着。……我们僵持着,怎么才能摆脱这种困境?”索尼娅则抱怨丧失自我:“我对你言听计从……我就是依照你的心意造出的一个复制品。”更直接的控诉假借海伦之口说出:“让我告诉你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吧!你父亲就当我根本不存在!他折磨我的方式就是当我是空气,装作不认识我。他在维也纳开讲座的时候,十天里他就不曾把我介绍给任何人。最后一天有人说‘介绍一下你的女伴吧。’他居然瞪着眼睛看着我说‘我不认识她,我根本不知她是谁。’我因羞愤而颤抖!”(此处十分明显,因为镜头立刻切换到克利夫无力地说:‘哦,莫莉,从我的思绪中走开吧。’)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小说里的每一个人都并不特定地、恒定地指代着某一个人,就像海伦可以是濒死的克利夫,也可能成为相貌酷似的莫莉,每个人都随时可以成为这个家庭其中一员的代言人。伍德福德刚刚成为伍德斯的第一幕,他变身成为大儿子,说:“你根本不爱我母亲,你将她一步步逼入绝境。”在餐厅里,伍德福德又突然变身大儿子说:“我想我的人生开端出了问题……有可能是我的童年……”在海边的长廊上,克洛德又变身克利夫,对他的妻子说:“你苦于自己的平庸。”
当这种思想的乱入达到高潮,很快,我们即将看到最有意思的一幕。丈夫拿着手枪干掉了臆想中的情敌伍德福德,但是通过乱窜的潜意识的旁白,我们看到的是,愤怒的亲生儿子干掉了爹地。这个时候,伍德福德变成了狼人(即将死的老人),温情地对克洛德说:“在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是一直爱你的。”这是暴戾的父亲难得的告白。但是没能挡住克洛德的子弹——用子弹来结束两个人的痛苦。
与“弑父”紧紧相连的是“恋母”。片中选择与母亲莫莉相同的演员扮演克洛德的情人海伦是别有用意的。最为明显的是,“儿子”克洛德与“母亲”海伦十指紧扣,成为情人。
“弑父恋母”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最为著名的理论之一,它所指向的是父爱缺失的一种心理环境。我们可以看到在强势、自私、暴戾的克利夫面前,克洛德的人格是受到了极大的压抑的(表现得顺从而黯淡),根源可以想象还有母亲的悲愤离世带给他更大的冲击。把这种性格分析戴上一个故事的面具,我们就得到了“弑父恋母”这样一出经典的隐喻。
至此一个温情脉脉的家庭分崩离析的精神世界已经完全解构。但是,合上书本,我们又回到了阳光下那个美满的温馨的家庭,父慈子孝,琴瑟和谐,事业有成。一个半小时讲了三个故事,雷乃真的是天才横溢!
同样是充满心理分析的意味,但是《天意》和大卫•林奇的《穆赫兰道》以及诺兰的《禁闭岛》有显著不同。后面两部片子的主旨是精神分析,但是这种分析通过隐喻来实现的,而在叙事上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连贯性。而雷乃虽然运用了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但是他更感兴趣的仍然是叙述手法和结构的实验。在《天意》里,我们看到时空上的参差、人物上的不对应,剧情隐蔽在文学性和自我感极强的叙述中,含糊而又暧昧。事实上,在十年后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这种破碎的叙述结构和迷宫一般的剧情更进了一步。
雷乃在电影里使用了一些道具来暗示“此处有玄机”,那就是随时随处可能出现的玻璃酒杯。每当倒上酒,小说中的人物便“突变”成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当海伦在长廊上倒上酒,就开始了对伍德福德的疯狂而尖利的指责(其实是莫莉对克利夫和克洛德的指责);伍德福德在高尔夫球场上莫名其妙地倒上一杯酒,就变成了怨愤的克洛德。这个手法在《穆赫兰道》里,大卫•林奇用的是蓝色的小盒子;在《二次曝光》里,李玉用的是水面。如果今天李玉在电影里用到这个桥段还能让一些人喝彩的话,那么30年前雷乃运用这些手段是多么令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