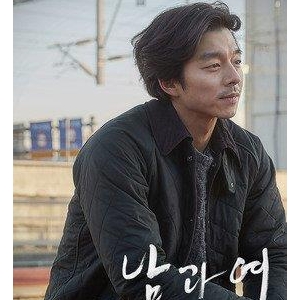《青年特尔勒斯》是一部由福尔克·施隆多夫执导,马修·加里瑞 / Marian Seidowsky / Bernd Tischer主演的一部剧情 / 惊悚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青年特尔勒斯》观后感(一):普通人的善恶
电影要表达的似乎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一书分析的是一个东西,同时还让我想到了电影《狗镇》。人性的善和恶都可以很自然的发生在普通人身上,人从一开始似乎没有好坏之分,只要人允许自己变成残忍、野蛮的畜生,善恶就没有界限。唯一的问题是有多大的可能性。二战中普通人的疯狂和集体野蛮似乎集中表现了这一点:这种可能性很大。
《青年特尔勒斯》观后感(二):电影与原著毕竟是两码事
感觉就是施隆多夫借这个故事来为德国那段历史找出一个理由。但是如果看了原著《the confusion of young toerless》,甚至去找Robert Musil的原著《Der Man ohne Eigenschaften》(没有个性的人)来看,那么就会发现穆齐尔的思想哪有这么浅显。道德或反道德其实根本上就是一会事。
《青年特尔勒斯》观后感(三):片末的那段话
“巴西尼跟别人一样是学生,一个正常人,他突然困惑了,在羞辱和折磨面前……我们必须要承认人从开始是没有好坏之分的,这是可能的,我们都在不停的变化,我们只因为我们的优点而存在,但要是允许我们变成受折磨的人或是畜生,那一切似乎都可能,就算最可怕的事也是有可能的,那样在好坏之间就没有界限了,完全融合在一起了,那正常人也也会做可怕的事。唯一的问题是有多大的可能性。我想知道这有多大的可能性,当一个人羞辱他自己,或是突然变的残忍,那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以前以为这将意味着世界末日,我现在知道不是这样的。那些看起来那么不可思议,那么遥不可及的事情,就那么简单的发生了,平静而自然,因此人必须要不断的警惕。”
《青年特尔勒斯》观后感(四):纳粹的童年
和《白丝带》一样,《青年特尔勒斯》也是试图通过回到更早前来理清纳粹滋生的原由:20世纪初奥匈帝国的寄宿学校=后来纳粹势力萌芽的德国;四个主人公分别暗示着两位纳粹分子(对被服从的迷恋、试图替天行道的意志,以获得感性的自我愉悦代替本该有的理性惩罚)、一位犹太人(被告知这样一个想法:只要你服从,就至少可以在外面活得体面),还有一位具有批判和反省意识的中间人:最后托尔勒斯的话深刻地揭露了纳粹能在以理性著称的德国萌芽的原因:一个人自我羞辱或一个人变得残忍,我们本以为是世界末日那样严重的事情,最后发现那发生的如此平静,因为好坏的转变是如此容易。在此之前他也曾抛出疑问:为什么身边人认为平常的事情,我却感到如此恶心?集体无意识的可怕在于它横扫千军的同时默默无声。少了自省和独立,法西斯主义就会不断扩大。
《青年特尔勒斯》观后感(五):勇气
你可能经常在脑海里幻想一些罪恶的事情,而且乐此不疲享乐其中,但当你真正面对这些事情时,你是否有勇气去尝试?你可能觉得你是个正人君子,一切邪恶与你不沾边,但当你真正深陷其中时,你是否有勇气说不,或者干脆和那些恶心的事划清界线独自清高?
青年特尔勒斯是那样的年轻,那样的英俊,可是他就正面临着这样的考验.他想彻底的远离那些邪恶的事情,可是当那个被欺负的男孩站在他面前时,他却拒绝了帮助他;当那个男孩再次被众多的手推来推去的时候,他也伸出了手,麻木无情的推开了他.他愧疚,他痛苦,这种矛盾折磨着他,慢慢的,他开始反思,开始反抗,但这一切只是换来了被开除离校的结果.
很羡慕特尔勒斯有这样一个母亲,当他离开学校的时候,坐在马车上,母亲什么都没说,一个温柔的笑,一切都被包容其中了.马车慢慢的走在广袤的土地上,悄无声息,直到结束.
《青年特尔勒斯》,“德国新电影四杰”施隆多夫(《铁皮鼓》)第一部独立导演的长片.一部对德国纳粹主义深刻反思的作品.
《青年特尔勒斯》观后感(六):从胜利的刀刃出发
“从胜利的刀刃出发”,这是我在一个恍惚的夜晚似乎完全睡着的状态下蹦出来的一句话。
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把尖刀。虽然我更希望这把刀是弯曲的,甚至能有漂亮夸张的曲线。可它从不让我得到任何美感,这把刀,像中世纪所有的冷兵器一样,坚硬地插进我的胸腔,这冰冷的质感,伪装得恶劣而又善良。也许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难得的灵感,也许我疯狂地撕裂胸腔,掏出这锋利的罪恶,但更多的也许是我平静地等待着汹涌的鲜血。可最终,我对这把刀已经没有了任何抱怨。
我不知道自己思考了什么,《青年特尔勒斯》让我明白了一小部分,但迷茫远多于觉悟。许许多多的迷茫包围着我,我甚至忘记了让我最清醒地个人的存在方式,以及更多复杂的想法。愤怒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代替了我理智的思维。我们总是这样,总是厌恶过去我们做的任何事,甚至痛恨愚蠢的字迹。它总困扰着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找不到任何出口,找不到任何能替自己开脱的借口。仿佛过去都是另一个人的,我记不清那样去做的理由。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我从不考虑理由,但,这是个让我不舒服的答案。
特尔勒斯不知道理由,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理由。
可我们不能从容地穿越过长廊,我们不能在殴打中得到放肆的快感,也不能用纤细的鹅毛笔记录这残忍的时代。于是,我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了。时间屠杀我们,欲望折磨我们,痛苦撕裂我们。但最终的结果是虚假的,火光一直在欺骗我们,诱惑着我们前行。我们向暴力屈服,并倒在它面前。
我突然明白,过去同样倒下的我已经四分五裂。
可是,当我不是特尔勒斯,当我站在最低的位置,当我失去所有能代表个人的东西时,我被所有的特尔勒斯旁观着,这感觉让我觉得很寒冷。我说不清让我寒冷的是什么,可它无数次地将我击倒在对自己的凝视中,检阅的目光让我终于看清不堪回首和所有困扰的根源。
但为何我又不能用清晰的语言揭穿它?迷人的哲学思想撞击着我,可怎么突然我又迷失在了这美丽的南方平原上?旁观,所有人的旁观连在一起就成了那把刀。
原来,我害怕的就是这把愚蠢的刀。
《青年特尔勒斯》观后感(七):托乐思的彷徨少年时
在这个平静、美好,被规则和秩序统治着的世界背面是否存在着一个黑暗、敏感,充满诱惑与恐惧的灵魂呢?在每一个年轻的生命走向“自我”的目的地时,他们总会遇到这样的困惑时刻,他们会发现理性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浪漫主义的激情更将自己引向了未知的深渊。罗伯特•穆齐尔于1906年发表的处女作《学生托乐思的迷惘》可以看做是对整个20世纪所经历的最初的迷惘期的书写,但它又仅仅记叙了一个奥匈帝国内一所寄宿学校发生的一件校园暴力事件。
作为20世纪德语文学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穆齐尔对这个简单的暴力故事的处理方式也预言了现代小说创作即将到来的革命。全书中单纯的故事表述极少,但却充斥着托乐思从旁观到参与再到反抗这件暴力恶作剧的复杂心理描写,而这些心理描写又涉及到道德、真理、正义、性启蒙、理性主义、反智主义、虚无主义、权力意识等各个方面。在托乐思的自我觉醒中伴随着理智与灵魂的战争,而这之后,整个德国乃至全世界也开始面对一场理智与灵魂之战,结果却是释放出了权力与集体暴力杂交而成的纳粹主义的幽灵。这被普遍看作是这部小说一次最伟大的预言。
在极具反思、思辨性的德语文学中,青少年发现另一个“自我”的途径往往是从受到周围人与物的影响开始的。在《学生托乐思的迷惘》中,托乐思来到一个全新的封闭式的寄宿学校,并且与信奉东方神秘主义的白内贝和崇尚暴力强权的赖亭成为了朋友,从而被卷入到一场恐怖的欺凌游戏中。在黑塞的名作《德米安》中,辛克莱发现“另一个世界”的途径,同样开始于一个神秘引路人“德米安”的出现。以往被忽略的黑暗世界在眼前展开,而对黑暗现实的发现最后又必然走向对自我的重新认识,这种痛苦的自我发现、自我审视,也渐渐开始成为了现代小说的创作主流。
在《学生托乐思的迷惘》里,一种全新的现代小说模型出现了。古典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互动往往是开放的,主人公需要走入到广阔的大千世界中去体验、感知生命的价值。从《荷马史诗》到《堂吉诃德》冒险的过程同样也是成熟的过程。但现代小说却反其道行之,人物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被异化,也可以说是被极端化了。环境在由配角向主角转换,人物也由广阔的环境走向了封闭的环境,并且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因为某些人、某些事而又无法逃离。托马斯•曼的《魔山》、卡夫卡的《城堡》无疑就是在封闭环境下探索深层主题的代表。《学生托乐思的迷惘》里那阴冷、高大的寄宿学校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刻画成一个巨大、压抑的灵魂空间,托乐思最后的离开也是逃出异化世界的暗喻。在1966年施隆多夫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青年托乐思》(巧合的是,这部电影也是施隆多夫的处女作,拍摄时他年仅27岁,而小说原著发表那年,穆齐尔也才26岁)的开头就是一个田野的空镜头,接着摇至托乐思和同学们在车站送别他父母的场景。此中寓意也就非常明显了。当然,由于小说本身的哲学思辨色彩,电影的改编就很困难,施隆多夫必须做出取舍,从这里入手来分析两个文本的异同也能反映出时代精神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电影对小说的改编主要涉及两处:一是班级对巴喜尼的处罚;二是托乐思与巴喜尼的同性性关系。先来看第一点。在1966年拍摄的影片无法脱离当时德国电影对纳粹的反思主题。施隆多夫通过放大集体暴力来暗示法西斯的历史教训,而因偷窃而被白内贝和赖亭抓住把柄进行暴力折磨的巴喜尼身上有明显的对犹太人的影射。作为旁观者的托乐思无疑又是当时德国普通民众的代表。这样符号化的人物设置确实与原著中的沉郁主题相悖,但也反映出德国新一代电影人的某种追求,即要用更深刻的表现手法来反思历史。关于第二点,影片并没有回避白内贝与赖亭对巴喜尼的性侵害,也没有隐藏托乐思的恋母情节和对酒吧妓女的迷恋,却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小说中托乐思与巴喜尼发生肉体关系的事实。究其原因,作为电影中托乐思所代表的形象来说,他是一个觉醒者,是一场良知与道德冒险中的幸存者,他承担着影片反思的主题思想。而小说里,由于时代不同,穆齐尔不会把反思历史当做主题,他需要呈现一个年轻人从肉体到灵魂的精神磨砺,当然这其中就包括这种匪夷所思的性体验。在小说中穆齐尔还安排了一段成年托乐思的独白来试图解释他与巴喜尼的关系。托乐思的回顾里诱惑与欲望在他看来并不矛盾,他承认“有失体面”,但又表示这些“少量的毒药”却又“必不可少”。托乐思把巴喜尼看作是“彼此共同携手走过整个地狱的人”。尽管同性关系成为了小说的重要一环,但这并不就是小说要表达的主题,它只是托乐思自我发现的体验方式,如同其它经历一样,是一次痛苦、迷惘的情感体验。
穆齐尔与那个时代所有伟大的、有预见性的艺术家们一样,在试图给 我们描绘人物的深层心理世界的同时,又不经意间展示出一幅病态的社会画像。从一个更加普遍的意义上来讲,某些感觉麻木或者运气够好的人总能无忧无虑地成长、随心所欲地生活,从来不知道自己只是在深渊的边缘徘徊。托乐思会迷惘、会彷徨,甚至“精神陷入迷乱,无法救治”,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青年特尔勒斯》观后感(八):孩子的残酷--蝇王与青年特尔勒斯
“不要恐惧你的敌人,
他们至多杀死你;
不要恐惧你的朋友,
他们至多出卖你;
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关心的人们,
只有在他们不做声的默许下,
这个世界才有杀戮和背叛。”
——————————————————雅辛斯基
如果要我从多部电影中寻找人类残酷的影子,一些片段会在我眼前浮现,譬如现代启示录中库尔茨上校之死与宰牛场景的交换出现,或者沉默羔羊中食人教授汉尼拔温文尔雅的用餐状态。如果要看人凄惨可怕的死状,战争似乎已经不能满足那些嗜血者的追求,惟有《德州链锯杀人狂》,《死神来了》之类的片子才能杀得血肉横飞,惊心动魄。
然而此时我要强调的,并非是形式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残酷,那种几乎扼杀人生机的悲凉与无望,那种让看客们槽牙发凉的感觉,当然,我不是指《咒怨》
我认为:世上最残酷的事,莫过于孩子的残酷,以及对暴力的熟视无睹,从孩子开始的腐坏,是人性腐坏的极限,犹如染上疾病的树种,扼杀了未来的整片森林。
《蝇王》原著威廉戈尔丁,电影讲述的是一群唱诗班的孩子在一次海难后流落荒岛,随着生存状态的日益严峻,原本良好的秩序与善良的面具都被揭开,形成了猎人与理性的代表拉尔夫的对峙。恶的代表:杰克,与善的代表拉尔夫之精神碰撞,拉尔夫是一名想要在荒岛上的孩子们中建立秩序的人。然而他最终的失势昭示着人们永不可能摆脱恶之阴影的结果。最终,理性的代表猪仔(piggy)与灵性的代表西蒙之死将荒岛上孩子们的最后一点良知泯灭,于是在荒岛上来了一场野兽与人的逃杀。
整部电影的基调忠于原著。威廉戈尔丁是悲观的,他的视点集中于人类面临极限环境以及不可知的恐惧时暴露出的丑恶,他们将精神寄托于偶像或者神明,将错误归咎于无辜者,将秩序打破,将人性泯灭。这样的一种兽性根植于人性本身,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露出爪牙。
《青年特尔勒斯》的导演则是德国新电影运动的代表施伦多夫,即《铁皮鼓》的导演的开山之作。根据罗伯特·穆希尔同名小说改编,来源于作者的真实生活事件的回忆,在20世纪处年奥匈帝国普鲁士东部的贫瘠的土地上,有着一所相对封闭的寄宿制学校,家长通过寄宿学校的严厉把他们培养成有用的人,老师严厉、刻板,孩子们有着欧洲寄宿学校的规矩,等级制度森严,暴力横行学校内的学生比亚斯尼经常因为曾经的偷盗行为而被同学选为肆虐的对象,他成为了众人暴力的牺牲品,特尔勒斯则是个旁观者,他鄙视比亚斯尼,却又反感残暴,当众人对比亚斯尼暴力升级学校当局为严肃校纪干预的时候,他的反应与众不同,此时的他并未为自己开脱,而是对善恶的转化做了一番论述,像旁观者一样的离开了学院。
此作以一种更为冷峻的方式审视了人性,将善恶的转换,性,人类的残暴融合在一起,像是一把冷峻的解剖刀,虽然主角有所参与,但他更像是一位旁观者,将一切尽收眼底。
或许我不该将《蝇王》与《青年特尔勒斯》做对比,但这两部影片的共性,都是未成年人之残酷。而其表现手法,颇有相似之处。
一,极端的环境,人性的实验室。
如荒岛之于《蝇王》,《青年特尔勒斯》也将故事的发生地点定在普鲁士边境,造就了一种与大社会相隔绝的环境,于是,大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理性,乃至信仰,都已经不能作为影响人们的准绳。毛姆将金银岛的勇敢少年染黑,利用死去的飞行员,爬满苍蝇的猪头,焚山的大火这些外部环境将拉尔夫逼上绝路。青年特尔勒斯则是用寄宿学校森严的等级制度,死板的管理,横行的暴力将少年的心灵掏空,他们会跑上阁楼看黄色画片,也会出去召妓。这些封闭的温室造就了这些变异的人性,将各种各样的丑陋放大,赤裸裸地摆在了桌面上。
其实我们也可以将《大逃杀》归为此类。
极端的环境往往会催生极端的人性,maslow提出了五种与生俱来的需求层次,在底层需求得到满足后,我们才会倾向于追求更高的层次的需求。生理与安全需求会出现在婴儿期,而归属以及自尊需求则会产生于青少年期,在这样的极端环境里,蝇王中的孩子们产生了自尊以及归属的需求,于是他们被一种群体的癫狂所左右,利用癫狂获得了自我认同,得到了战胜恐惧的快感。而青年特尔勒斯中的老大拜尼尔克,在封闭与教条森严的环境中通过掌控与玩弄比亚斯尼获得了自我认同,一帮从众的无知少年,通过拉帮结派获得了归属感。最终的善的惩罚在比亚斯尼被吊起中升华,成为了群体的暴力之恶。
在设置这样的人性实验室时,两者不约而同.不得不让我感叹,危难乃是考验人类品格的试金石。
二,集体无意识与斯德哥尔摩情节。
“集体无意识”是人类的一个思维定式。一件事情明明有违道德甚至是违法犯罪,一个人可能不会去做,但是如果一群人中有人已经做了,并且在没有产生相应后果的时候,就会使人们产生非理性的思维,于是我的无意识、他的无意识,以及众人的无意识汇聚成流,造成了使“不正常”现象成为“正常”的“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有许多种,有对罪恶的集体失语,有对不良现象的集体麻木,有对违法事件的集体参与。比较典型的如聚众哄抢财物、球迷闹事等等。
不难理解,在荒岛上的唱诗班孩子们为何会在癫狂中选择了成为猎人,心理对群体的归属感以及成为野兽后那种挣脱束缚与恐惧的自我认同感将他们推向了猎人的集体,于是,当这个群体越来越大时,人性也就越来越麻木。
同样,《青年特尔勒斯》中在比亚斯尼被学员们推搡,吊起时,尽管特尔勒斯非常厌恶这种暴力,他还是将苦苦哀求的受害者推向了人群。
集体无意识的倾向,并非是人类可以文过饰非的遮羞布,这让我想起兄弟连中,E连进驻一个德国小镇后,德国老人们不屈地昂着头,可就在他们在小镇外发现了一个集中营的濒死犹太人的惨状后,要求这些德国居民去搬运尸体,老人在E连战士的逼视下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漠视,同样是犯罪。更何况,这些犯罪的主体还是孩子。
这种集体的漠视,甚至犯罪,暴力的受害者,往往不会反抗,甚至对犯罪的主体产生了认同,这样的斯德哥尔摩情节,在影片中也随处可见,唱诗班的双胞胎尽管对猎人的行为不认同,最后却也成为了从犯,而比亚斯尼慑于拜尼尔克的威严,最后也行使了偷盗的行为。
我们可以将其归咎于人性的内因,随着人类的发展,我们根植于基因中的趋群性是不可磨灭的,可这并不能成为暴力与残酷的借口,因为人类之于动物最大的不同,正是人性的存在。把握住这一点,两部电影都重重地拷问了人性。
三,旁观者,主角的存在感
我们可以说拉尔夫与特尔勒斯是同类型的人,理性,善良,抱有美好的愿望,敏锐的观察力,以及,身体条件上的弱势。
拉尔夫与特尔勒斯直接参与到故事中,而非一个完全的旁观者,以人的角度将所见所闻所感传达给观众,之于拉尔夫我们可能感受到的是偏重于参与者感受的人性泯灭天真不在的切肤之痛,之于特尔勒斯,则是完全脱离了参与者的视角,极为冷峻地指出,善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极大的善可能转化为极大的恶,绝对的人性并不存在。回答了这些问题后,他抽身而出,毫不犹豫地离开,走向人生的下一站。
一部电影的主角,应该是贯穿主线的人物,两部作品主角形象类似,却不尽相同,一个是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最终成为被放逐者,另一个则是追随者与旁观者。但两个人物的寓意是明显的。他们都是事件本身那些被被压迫而式威的善之代表。在世风日下时,他们都是逆流而行的直言者,但他们不是基督,最终没有拯救受害者的力量,这样的人物的存在,也许正是为了警醒那些祈祷救世主出现的却无行为的盲从者,正义,不会轻易到来。
四,象征意义
《蝇王》是一部残酷的寓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的孩子们,本身就在一场可笑的大人战争游戏中落难荒岛。而象征者秩序权力的海螺,象征着文明的火种,以及每个孩子心中的梦魇--蝇王,以一个爬满苍蝇的猪头形象出现。随着人性的兽化,海螺象征的秩序被打碎,文明的火种被熄灭,唯一一个善良而类似先知的人物西蒙被蒙昧与野蛮杀害。于是灵性皆无,众人盲从,蝇王获得了胜利。而西蒙早已经指出:“恐惧来自人类,可怕的是你们的心灵。”
此时我已经不想将影片的反派杰克与希特勒类比,尽管他们在人群绝望时蛊惑的方式,咄咄逼人的态度,疯狂而野蛮的野心如出一辙,你可以将他的模板赠予独裁者,战争疯子,邪教首领,可当你深入地看他,却看到了镜中的自己。因为我们往往被自己本源的兽性所迷惑,迷失。
这其实是一部寓言的人类史诗。先进的民族总是为蒙昧与野蛮的武力所征服,于是历史一再倒退,复又前进。
与蝇王相比,青年特尔勒斯则更趋近现实,导演将实验室放置在旧普鲁士边境的一个寄宿学校,用一个被欺负的孩子的事件直观的让人们联想到了德国民众在经济危机中旧政府权力式威,希特勒带领的军阀政治将矛头转向积累财富的犹太人,就这样,盲从者,攫取利益者,嗜杀者,以及被胁迫者都被绑上了纳粹的战车,开始了残杀,掠夺,开始了征服与欺压,
提到这所学院,我不能不想起在纳粹二战中出现的napola,以及希特勒青年团。他们的共性,同样是让孩子从小就被灌输纳粹主义信念,最终成为战争列车的齿轮或者征服世界的后备军。
片中常常有烟斗烫白老鼠,笔尖戳死苍蝇,屠户杀猪等场景,这些日常生活中人们熟视无睹的行为,就成了德国全民残酷反犹的象征,因为当时的人们,已经对这样的行为习以为常。
男主角在老师面前的表白导演论证了自己的对世界的看法:善与恶存在在心灵深处,是生命的的两面性,一个人不会绝对的坏和好,人是不断改变的。我们寻找相同类型的人,因为影响而改变,任何可怕的事情都会发生。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他们相互渗透。这实际上是导演站在德国人的角度上对战争人性的一种反思。也是对所有过去的罪恶以及未来的可能所作出的评述,我们所要避免的,正是从孩子开始的这种恶之倾向。
这两部电影,都难以带给看客任何快感,在当今充斥着肥皂剧情与劲爆场面的荧幕上,更不可能出现,可是,每当我看到新闻中非洲战场上的少年兵,人体炸弹中的妇孺,我还是能清晰的回忆到电影的每个细节。因为孩子,正是所有人类的未来,而这些电影,正是提醒我们不要堕入修罗道的警钟。
鲁迅曾经在狂人日记中大喊:救救孩子!
可能,我们首先要救赎的,是自己。
原载于 MOVIE VIEW BY JABBERW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