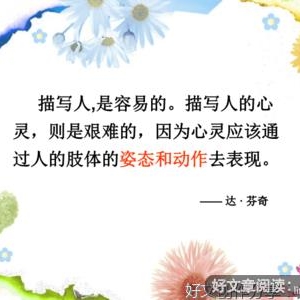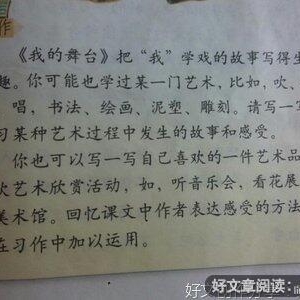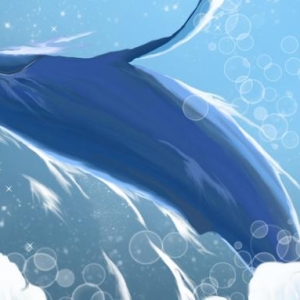二元店,买指甲剪,不禁想起老艾。
老艾是谁?他和我不是一个村儿的,可能和你也不是一个村儿;他与很多人都不是一个村的。
但他的一件事儿传到了我们村儿,就是他跟自己女人结婚三十多年,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不在一起睡、不在一张桌吃饭,他们分居了十年。
我很佩服他那与爱情长跑背道而驰的执拗。
老艾是个诗人,顶大的诗人,比我们村长还有名。
所以,他又有了第二个女人……
老艾写过一本诗集,叫《四个四重奏》,在县里得过大奖。他最得意自己诗集里的一句话:
吾之伊始,即吾之终结;吾之终结,即吾之伊始。
他写东西的时候,落款从来不写老艾,却认真的写上T·S·艾略特,我一直觉得他挺会装洋蛋。
从老艾那句诗里可以看出,他跟我一样,都喜欢那个什么梅的《终结者2》。有多喜欢,他把那句话作了自己的墓志铭。
这一点,我自叹不如。
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那部梅什么的电影,但我不确定老艾为什么喜欢那句话,可能因为是他自己写的。
我猜,我只能猜。归其根、结其底,电影里的一些东西和诗里的某些东西有些许的趋同;即干掉旧的我,才有新的我;新的我变成旧的我,再被新的我干掉。
是这样吗?我不清楚。或许,仅仅因为它们都牵扯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时间。(即从彼时到此时之间的全部)

往大了讲,它是宏观上的维度,囊括所有物质实体和精神建筑。
往小了讲,它其实也不大,无非就是感官的产物;是人这个小圈子里的一种自我实现的说法(量化生和死的距离)。
另外,(接吾之……巴拉、巴拉……没有小魔仙)亦语同于家乡五里外小寺的和尚,他也曾懒懒道:
俺上山,就是俺下山;俺下山,就是俺上山。大概都在说,开端永远是与终端无缝钢管般衔接的。
同理,总有人上山砍柴,也总有人下山买米(佛说轮回,科学说循环,没主什么事儿)。
所以说,从哲学年鉴上往下捋,老艾的苦思与试图突破二元壁的想法新颖吗?不。
那不是专属于西方的经典二元论,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有产阶级的精神困境。
世界是二元的吗?不,我想没那么“便宜”,起码不会像二元店的指甲剪那么“便宜”(便宜的东西都很简单)。
世界一定是二元的吗?不见得。毕竟,还有三元催化器不是,还有四元玉鉴不是。
二元矛盾吗?也许。二元一定对立吗?也许不。你看道教太极图里的黑白双鱼,看似黑白分明,却又凹凸合抱,从不两立,反倒自成圆满。
正如老艾诗里常见的关键词,刹那与永恒、死亡与新生、过去与未来等等,本就是道佛两家的探索课题,不知道熬走了多少得“道”高僧、世外高人。
二元是共存的吧!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哥们儿姐们儿谁不是右手执矛,左手扛盾。你戳我挡,你来我往的,热闹极了。
当然,也允许左手指月,右手揽腰(什么腰子或谁的腰不重要)。
老艾一生,目睹了人类这个“小圈子”的两场大火火拼,就是一战和二战。还经历了首场三十年婚姻十余年分居的“成年不幸”,难说他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会不会深以为意。
凡此种种一路走来,四重奏里便再也不会是对酒当歌小蜜蜂,绿肥红瘦海棠花的款款深情、情深几深;而是叩弦观苍月,捉剑问天人的深沉了。
故,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不对,你读我读老艾的诗,艰深、晦涩、难懂(也许你是985大学霸,你懂?不一定的)。但凡数学底子不太好,乍看一如觐见二元一次方程,那叫一个大小脑红蓝频闪。
用00后的黑话,叫:CPU都干烧了……
尤其,你倘若不知四重奏是以同系四模乐器作为基本结构的乐曲形式而得名的;便更不得其法,光看书名都得稀里糊涂。顺便提一嘴,四重奏它爹叫海顿,弗朗茨·约瑟夫·海顿。
是的,这是个声乐专业的经典概念。为什么要这么说,大概老艾想表明一点,哥是懂节奏的。
那么,四个四重奏按照“圈内人”的评价来看大概是这样:
词之配合,不可谓不默契;语之意境,不可谓不超凡;诗之用心,不可谓不纯粹;哲思下潜,不可谓不深邃。
那细化到读者个人,到你呢?你闭嘴,我不想听……(开个玩笑)到我了。我直接说:
老艾中后期,有一个身份认同的转变,即从一个没有历史的空心国美利坚到祖籍大不列颠的保皇、古典主义及回归英国国教。这兴许是大多数追索者的成长规律,当然也可以说是“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撞完南墙撞北墙。”
很多宏观上的事儿,许多微观下的人都在随着时间的不断散射和膨胀而转变。那些文学解决不了的,走进科学,科学技穷的,奔赴哲学,哲学无力的,去贴宗教(玄学)。
万物归玄是仅有的路,毕竟后面是一道一道的南墙北墙,没有别的选择(人类和狗的选择都不多)。

那老艾在四重奏里究竟弹了什么曲子?他对他们说了啥?
我有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不知当讲不当讲的都要讲几句:
有人说是春、夏、秋、冬,四季轮换,万物更迭的幻灭与寂然;四个季节呼应了所谓的“四”。
也有人说空气、水、火、土,一数也是四;四重奏意味着四个生命的主要原素在构成与坍塌中突显了人的神性与神的不可究极诘。
我不敢说没有或不是,但这有些局限了。主观上讲,我看到的只有时间。客观上,每一双眼睛都将看到一个突兀的大概和那些隐藏的细节。
时间,是这部作品的全部张力所在,无论细节往哪个方向突围,它们都不会离开时间本身。
老艾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回溯了他想要到达的那个原始的即为个体又作复数形式的生命起点,以及终点上的一切。
其欲求超脱于狭隘的时间线性概念,从不同的位面去感受人、事件、消逝与生长的神秘与不可探究性。
在散乱的意象世界中,他渴望走近时间的边界,与历史对话,去感知物质与精神二元共存的蛛丝马迹。
然后,不遗余力的去一场向着人间的告诉:
世界以我发生,以我结束;时间以我伊始,以我终结;世界以你发生,以你结束,时间以你伊始,以你终结……
那不是同一个故事,也不在同一个地方;那是在燃烧的诺顿或小吉丁,也在唐古拉或乌兰巴托;那是漫长冬日的一场战斗,也是滂沱大雨里的一次奔走。
可它们都在同一个时间的散射面上,犹如陀螺一样不停的旋转……
—— 结束——
阅读书目: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