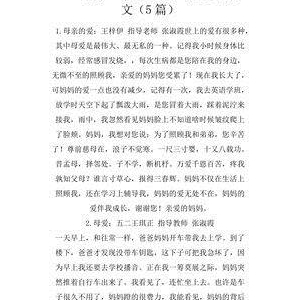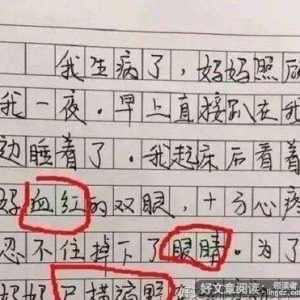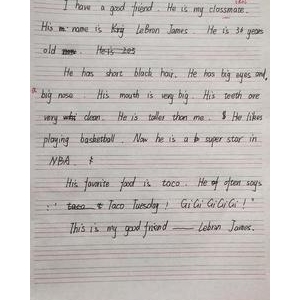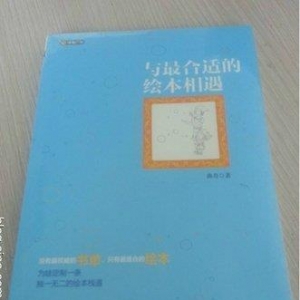在我为数不多的写作生涯中,这是第二次给毛姆的作品写读后感。(上一次是《月亮与六个便士》)为什么总是毛姆呢?我想原因大概是这样的:毛姆称自己是二流作家,当然这绝对是一种非常谦虚的说法。而我读他的书,总有一种老妇人听白居易的诗的感觉:语言流畅而形象,非常浅显易懂,内容生动而立体,使人印象深刻,这种画面感是任何影视作品所带来的视听感受而不能比拟的。反观其他文学巨匠,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奈等,这些伟大的作家一样能给我带来前所未有的思想风暴,但我总有一种把握不定的感觉,以至于有很多次,我执着于打开的空白文档,勉强写下几行文字后,感慨虽多却最终没有写成。这也只能归结为:以我目前的修为水平是不足以驾驭这样文学经典,从这个角度看,毛姆确实是个二流作家啊。
写这篇文章的最大初衷是我发现《刀锋》这部作品似乎可以用来解释月亮与六个便士的矛盾冲突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问题),虽然毛姆的这两部作品都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但他从来没有给出这个问题的明确答案。从我们每个人审视的角度出发:看山似山、看水似水,山水就在那里似乎永远也不会变化,可每个人眼中的山水却又不尽相同。而我看到了这个问题的解释方法,灵感虽然不完全来源于《刀锋》,但它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以及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借用这部作品的主题,结合自身感悟,我将尝试寻找月亮与六个便士的矛盾冲突的问题的答案!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给某个作品写读后感之前,会先在网上查阅相关的读后感,看看其他人的感受能否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灵感。其中一个人是这样评价《刀锋》的:它就如同黑夜里熊熊燃烧的火把,即便你正处在极端的黑暗与失落中,它的光芒也能彻底照亮你的灵魂。这个评论如同作品本身,非常能给人们带来光明与希望。书中主人公拉里的形象,是臻于圣人的形象(但绝对没有达到圣人标准)。他可以在完全没有功利主义的影响下,于巴黎读书很多年,而且读的大多是以斯宾诺莎为代表的,没有显而易见实用性的哲学书,这些既不能转化成钱,也不能实现所谓的“人生价值”。多年以后,书中的毛姆问拉里 “你在巴黎读了这么多书的收获是什么?” 我得到了最能使我感动的回答,拉里说:“一无所获!” 无用之学,果然是哲学的最高境界啊!
不过这也就是说,他不但没有获得世俗意义上的价值,连他自己的修为修养也没有获得任何提高,只是白白看了这么多年的书。
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则寓言故事,大意是:一只猫经过多年苦修,终于练成了8条尾巴,只要再多修炼一条,就可以列入仙班,完成修行。一天,佛陀前来度化这只猫,佛陀说:你会面临一个考验,你需要去满足一个人的愿望,可是每实现一个人类的愿望,你就必须以一条尾巴作为代价。如此一来,第八条尾巴长出来又消失,陷入了死循环当中。这只猫遵循了佛祖的教化,不断的帮人们实现愿望,不断失去尾巴又再修炼尾巴。这时候的猫像极了正在求学读书的拉里,发奋努力而一无所获,直到有一天,它遇到了那个愿意让自己的愿望是让这只猫能长出第九条尾巴的人,至此,一切功德圆满。
其实在追求智慧的这条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只猫,有的人机缘巧合可以获得开悟,成为人们口中相传的圣贤之人;有的人终其一生,不断的循环往复,却没有丝毫的进展。但是,正是这后一种人,才是我们这些普罗大众的“俗人”可以学习并且适当模仿的。因为纵观全书,我也不认为拉里已经成为了第一种人,他只不过是在寻求智慧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的第二种人。他可以散尽家财,以现代的方式“托钵乞食”来追求自己心中的灯塔,第一种人应当被供奉在神坛上,可第二种人才是照亮我们内心的原动力。
按理说,这两种人应该是一种人,只不过一个到达了智慧的彼岸另一个没有,或者通俗的说一个成功了另一个没有,就要划分成两种人,我是不是太有点以成败论英雄了?这就要先讲下我个人对这个成功的定义与看法:在寻求智慧的道路上的成功,一定是寻求到了最本源的智慧,佛家叫做开悟,我们的传统文化称这样的人为圣人。就以我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浅显认知来看,中国有三个圣人在文化脉络上非常重要,第一个是孔子,他老人家最大的功绩是把我们人类与野蛮的动物分离开,从女娲的盘古开天到伏羲、周文王的易经八卦,从这些上古的天神文化到落在地面上成为可以触碰得到人间文化,孔子给我们带来了各种礼仪规范与非常积极的入世哲学构建起整个社会结构的文明化,这种影响至今在我们的血液中流淌。但是,儒家的思想虽然能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却不能解决超过现实以外的问题,例如生之前、死之后这些,随着魏晋南北朝佛教的传入,儒家的阵地逐步失手,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人纷纷加入佛教阵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认为的第二个圣人出现了,那就是朱熹。
他以“存天理灭人欲”观念,配合“格物致知”的探索方法,为儒家学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操作的成贤之路。可以说是给传统儒学的理论打了一个强有力的补丁。而朱熹为啥可以成为圣人?除了他为儒学挽回了前沿阵地的贡献,更是因为他的一生是以身体力行来践行自己的理论,据说他在逝世的前一天还在修订《大学》。这有点像近代物理学家玻尔,人们发现他去世前一天的黑板上,画着爱因斯坦的光盒实验的示意图。这样的人怎么能不称之为圣人呢?
但是,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圣人,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圣人存在标准?这就要引出第三位圣人--王阳明,这位王圣人从小的人生目标就是当圣人,无论是在很早的时候就表现出来的学霸气质,还是再到后来各种功名、奖项拿到手软,再有后来的落魄被贬,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人生目标--成为圣人。直到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在贵州龙场,一道闪电刺破黑暗,王阳明睁开双眼,他知道,他的目标达成了,他成为了圣人。——没错,这就是成为圣人的标准!成为圣人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就是:自己明确地知道自己成为了圣人。而在他作为圣人之后的日子里,无论是平定宁王的叛乱,还是传授心学,还是在做任何事情,他都能保持内心与外在和谐的一致,举手投足透露出的安宁祥和以及给予弟子与后人的无限启迪,随而将中国的文化主脉络由朱熹的格物,转向向内的求心,所有的这一切,才构成了圣人的存在。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就是世尊佛陀在菩提树下发了若不成佛誓不起坐的誓言 ,经过七天七夜之后,佛陀起身,也就是宣告自己证悟成佛。觉悟者是一定知道自己就是觉悟者。而且在成为觉悟者之后的日子里,举手投足、一言一行甚至连身体最微小的动作也能给人们带来无尽的安宁、祥和与喜悦。所以,第一种人与第二种人的相差,可能不止是一生一世的距离。
其实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最大的担忧就是:这篇文章会涉及一些佛学的思想,而我又从来没有认真的研读过任何一本佛经,恐怕自己的水平支撑不下去。道听途说的佛学理论加上抖音剪辑过的印度连续剧《佛陀转》就是我的全部理论基础的来源。能让我鼓起勇气打开空白文档的动力来源于六祖惠能,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是“顿悟”的宣誓,也是我勇气的来源,惠能大师能以不识字的资历背景获得弘忍大师的认可成为禅宗六祖,而才华横溢的神秀和尚以及他所倡导的“渐悟”只不过是这段历史的背景色。那么,我这个不学无术的小白也想要把心中印证过的道理书写出来,至少我是追寻了内心的指引。
虽然是这么个情况,但是我也做了一点功课,在写这篇文章期间,我读了黑塞的《悉达多》(悉达多跟佛陀重名,但是书中的主人公悉达多跟佛陀是两个人,后续提到悉达多指的就是黑塞的悉达多)以求获得更多感触,刀锋之所以锋利,那是要用来切开未知与迷茫,所以不管是悉达多还是拉里,他们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找内心里的“阿特曼”。我想大多数读者都跟我一样,读《刀锋》的前半部分,会有无数个问号指向拉里,他到底在寻找什么?作者毛姆也并没有卖关子,在前半部分已经尽可能完整的记录了所发生的事实。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看起来波澜不惊,又有点云里雾绕,更多的是傻里傻气,然而就在拉里看到湿婆神像,心中涌现出“梵”,至此,不光是拉里,还有我们这些读者,终于明白了他在找寻的究竟是什么。
拉里是一个臻于完美的人、臻于圣人的人,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伊莎贝尔,她是一个美丽、端庄、大气有涵养,为了生活的精致而积极追求的女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真的谈不上对错,拉里跟伊莎贝尔就是月亮与六个便士的两端,肯定有很多读者可以罗列一大堆理由来证明伊莎贝尔的生活方式是如何正确,对此,我深表赞同。但是如果只是为了彰显六个便士的普世价值,那么拉里的光辉要在何处闪耀呢?这就是月亮与六个便士的矛盾冲突问题的核心之所在。
在要阐述这个核心问题之前,请允许我先简要说明下我的世界观。在很多年前,考研给了我极大的心里创伤,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却依然差的很多,这种绝望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我只记得在走出考场的那一刻,一个坐在楼梯尽头的背影,那个人用双手捂着脸深陷在两腿之间一动不动,我快步从他身后走过去,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谁,但这个背影永远烙印在我心里。考试前的每一天,身体与精神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有一次,我跟一起备考的同学抱怨说:“我觉得最让我学不下去的就是政治这门课,哥们我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现在让我强行灌输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些东西,我是骨子里有抵触啊” 现在想想,其实我是更倾向于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一,一就是上帝” 即自然就是上帝,所以佛陀也好,真主也罢,这些名词都是梵的具象,只不过我心中笃信有这样一个存在,这个存在一定不是具象的,也就是我自己标榜的客观唯心主义中的客观。传说佛陀拥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在世时的形态都不是具象的,似乎也是更能说明这个问题。所以人们经常在寺庙里求拜的佛陀塑像大抵只是为了传法教化众生的一个方便法门吧。或许有一天,我可能会用佛陀所说的一句话去阐释一个道理,又或者是其他圣贤所说的,但这个道理一定是要经过我自己印证过的,这样才能是属于我自己的梵。但这些并不准确,因为所有的语言文字,只要是能说出来、表达出来的意思,都是有噪音的,包括那个获得了无上真理、拥有正等正觉的世尊佛陀也不能用自己的言语来表达他想表达的所有含义。这么看来,佛陀就是那个生活在更高维度的人,正如一个三维物体在二维平面上投影,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穷极一生研究二维平面上的形状,也很难勾勒出三维全景。所以,黑塞笔下的悉达多要离开佛陀,把自己置身于红尘与欲望中腐蚀自己的灵魂与肉体,以自我毁灭的方式,使得那个“我”渐渐沉沦下去,而那个“阿特曼”才能逐步浮出水面。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获得证悟,就拿伊莎贝尔来讲,无论从那个角度看,她都没有任何可以让人指责的地方,她追求美好的生活,相夫教子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她虽称不上善良,但绝对不邪恶,这是一个平常人所能得到的相对完美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看似完美的生活画卷只是三维在二维上的投影,如果尝试的用高一维度的视角去看待这些,那么我就必须要引入一个非常唯心的概念——“轮回” 正如毛姆所说,东方人相信轮回,是在血液里相信,书中那个印度的高官可以抛弃妻儿财产,一个人托钵乞食,如果不是坚定的相信轮回,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这也是不相信轮回的人们眼中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伊莎贝尔可以一直活下去,她的青春与美貌以及财富可以永远、永远的存在下去,那么她在享受了无尽的人世间的美妙,丈夫以及儿女都在无比健康幸福的环境下陪伴她,之后的她将获得什么呢?一定是无聊!叔本华说的对:“人生就是一团欲望。当欲望得不到满足便痛苦,当欲望得到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摆荡。”
这句话看似很悲伤,让人们看不到任何希望,但是要是从轮回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都会经过无数次的轮回,最终要到达的彼岸就是梵。或许拉里的轮回次数比较多,也可能是在之前的每个轮回中都在积极的探索,其实他早已享受过人世间的所有欢愉,而无聊感愈发的强烈,所以才能如此的专注寻找他之前轮回没有找到过的那些,寻找那个除了“阿特曼”以外再也不能给他带来新奇的东西。每个人的轮回资质不一样,不可能强求每个人都像拉里那样活着,所以伊莎贝尔才是普通世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要记住拉里的样子,因为若干次轮回后,我们终究要活成那个样子。
按照轮回的假设,似乎可以完美的解释月亮与六个便士的问题,可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特别引起注意,尤其是它还可能引发另一种极端。之前流传过一句“毒鸡汤”,很多人抱怨说:我们懂得了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这有点像东晋时期蔚然成风的玄学家们,这些人衣食无忧,(大部分是)拿着国家的高额俸禄研究那些玄而又空的学问,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该有人去研究,哲学本身就具有这些气质,而是说这些人身居要职却尸位素餐,拿着国家的供给却什么正事都不做,那么,只会空谈这些理论的人又怎么能过好这一生呢?生活在这样社会结构下的人又怎么能幸福呢?从这么看,拉里下井当过矿工,干过汽修工,还准备要去纽约开出租车,并且说:读上一段时间的书就需要去干干体力活,这才是脚踩大地的修行法门,而就算是佛陀,也不是整天都在讲经说法,他每天都会带领众弟子一起托钵乞食。精神世界无论多么精彩绝论,在进入《大般涅槃经》之前,你还是要跟这个世界有足够多的联系。而就算是高更,也是需要吃饭的,他不是差点就被饿死了吗?千万不要像有些人在躺平这个名词前面加个“佛系”,并称之为佛系躺平,殊不知佛陀讲授的八正道,其中之一就是:正精进。
佛学或者其他哲学,绝不是消极、懒惰的保护伞。而恰恰是在人世间这个广袤无比大学堂里,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是在修行。对于像我们这些轮回水平还比较低的人,挣钱就是最大的修行:以世俗的一般标准,“挣到钱”说明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正向价值,而产生价值的同时也修炼了我们自身,所以要通过努力的学习、工作、以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一切顺利,就有可能产生高级的无聊感,就有可能在追求阿特曼的道路上,迈上一小步。其实神秀的“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也是在说这个问题,渐悟是在强调人这一生需要多多努力精进才能见到佛法,顿悟则表达了佛性的成果是由无数次轮回的努力精进而产生。这两种说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对立,并且神秀的主张对普通人来说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正如佛陀所讲:不追忆过去、不妄想未来,专注当下的每一刻,那么这一刻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我们每个人也才是真实的。
所以,专注而努力的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即见如来”的不二法门。就我而言,我一直希望通过努力挣取很多的钱,这些钱多到可以让我不用工作而不用为生活担忧,并且请的起一位家庭教师来教我算《高等数学》。当然,目前这个欲望对于我来说是种痛苦,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排除带来痛苦的杂念,专注回归到眼前的每一件事中。这或许就是只专注于呼吸的冥想,佛叫做禅的实际应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