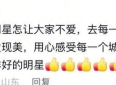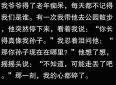25年前,一部经典横空出世,它恐怖、惊悚、悬疑,它峰回路转,震惊世人。
它让初出茅庐的导演一鸣惊人,它让受制于类型片的猛男不同以往,柔情万分。
它是M·奈特·沙马兰、布鲁斯·威利斯、海利·乔·奥斯蒙的[第六感]。
而今到了2024年,M·奈特·沙马兰正在为下一代(他的女儿们)保驾护航,他本人的创作则处于不温不火的阶段。
布鲁斯·威利斯身患失语症,更被确诊为额颞叶痴呆。怎叫一个唏嘘感慨。
至于海利·乔·奥斯蒙则和那些年传说中的童星一样,成为好莱坞名利场又一个“消失”的人。
岁月是把刀,但它唯独不能伤害电影分毫。
25年过去,不知沙马兰是否感叹岁月的力量,虽然于他不免有出道即巅峰的评价,但这位印度裔导演以最独特的“第六感”为“千禧年”恐怖片的承前启后,书写了重要的一笔。
今天继续人·鬼·事,继续[第六感],继续人间情。
微妙的距离感
马尔科姆与科尔的第一次面对面是在教堂。
回头再看,这是一个明显的暗示。
注意看马尔科姆与教堂环境之间的镜头,通过虚实处理,角色与背景产生了明显的割裂感,就像是不太细致的“抠图”,仿佛他是被粘贴到这个时空的。
他坐着,假装在自言自语,通过教堂座椅,他与科尔也被分割开来。
这种分割在后面的故事里,通过各种方式,得以强化。
但是由于成功的铺垫,这种“生死界”的区隔始终可以被解释为“距离感”,而这正是英雄人物心理医生要挑战克服的。
两人的第二次见面就是为强化这个方向的距离感而展开。
这个场景以母亲琳恩与马尔科姆的对坐开始。
原本很均衡的取景因为近景处座椅的比例产生了不协调,两张椅子的连接处正好形成了一条“竖线”,将马尔科姆“切”了出去。
再看两人的眼神,马尔科姆注视着琳恩,但琳恩却在发呆。
更能展现两者“距离”的是琳恩的坐姿,她一只脚随意地弯在椅子上,这显得相当随意。
当面对可能解救自己孩子的医生,这种随意即便不说不合理,至少不正常。
接下来是对话。
母子二人直接进入了日常的闲谈,琳恩完全没有要介绍医生的意思。
当然,到此为止我们依然可以自行脑补,如治疗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并无起色——配合之前琳恩遭遇的一系列灵异场景。
接下来的“向前向后游戏”是全片的精华之一。
当科尔站在毯子上时,他与马尔科姆的实际距离并不远,但通过的大角度镜头,房子的空间感被放大,间接拉大了两人的距离。
游戏从中景开始,随着猜测正确,两人的距离拉近,镜头也变成了近景。
但是随着后面连续猜错,摄影机与角色之间拉开了距离。
不是通过剪辑,而是通过摄影机本身的移动,这是模拟科尔的“视角”,而“原地不动”的人,是这个以为可以提供帮助的医生。
在之后一个与妻子的场景,马尔科姆解释了关注科尔的理由:
与枪击他的病人太相似。
此处两人几乎没有物理距离,但在关系上,显得非常遥远。
于是,正确的信息(马尔科姆帮助科尔的动机)与画面合谋让观众得到了错误的信息(夫妻俩关系破裂)。
随着科尔自己的表现越来越诡异,我们越发觉得科尔有问题,而这个问题不是心理医生能够解决的,那是“招魂”的领域。
大书桌保持了距离感,而马尔科姆的魔术表演让科尔说出了重要的台词:
这不是魔术,硬币一直在那。
这其实是在说真相一直在那。
作为公平信息的作者,希亚马兰没有隐藏证据,他一直在双线并进。
在希亚马兰客串出演的医生的场景。
被逼得神经衰弱的母亲琳恩被导演拉下水,成为新的误导角色。
她当然没有伤害科尔,但在这类故事里,最后母亲要去伤害自家娃的桥段可太多了。
恐惧使人疯狂,也使人易受摆布。
在这一幕之后,科尔说出了最重要的台词:
我能看见死人!
故事开始明显地向灵异恐怖片的方向发展,正是这种合理地揭秘,把另一个秘密掩埋了下来。
也是在这场戏中,两位主角的距离感在另一种情节框架里已经消弭,无论镜头分割还是场景分割都变少了。
当然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当代观影量的易累积催生了更敏感的观众,25年后的观众们早就被训练地对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作为一部并非开放性、多解读的惊悚片,揭秘的重点也不是这很难猜,而是编导如何思考和布局。
超越第六感
海利·乔·奥斯蒙是世纪末的一大发现。
按照希亚马兰的说法,如果没有找到奥斯蒙,那么这部电影可能拍不下去。
一开始,他还觉得奥斯蒙过于漂亮了,可能不适合影片的氛围。
后来揭秘他得到角色的三个理由中,有一条来自选角导演,她认为奥斯蒙的脆弱感正好;
还有一条来自经典的“明明可以靠脸,竟然还这么努力”。

希亚马兰问他是否仔细读了与他角色有关的剧本,奥斯蒙说读了三遍。
希亚马兰对此已经很惊讶,当奥斯蒙进一步解释是读了整个剧本三遍,希亚马兰只剩下叹服。
至于最后一条,则是因为奥斯蒙是试镜中唯一戴领带的男孩(片中的学校穿着有领带)。
这次成功试镜对奥斯蒙的影响不止于此一部成功的电影。
当时斯皮尔伯格正努力把库布里克的[人工智能]搬上银幕,里面同样需要一个“问爱”的男孩。
考虑到凯瑟琳与老斯的长期关系,这样一次在眼皮底下的耀眼演出,显然有助于他更进一步。
另外,更早几年饰演的“小阿甘”同样功不可没,导演泽米吉斯与主演汉克斯都是老斯的好朋友。
此外,当马尔科姆选定布鲁斯·威利斯,两人的对比就为希亚马兰的误导提供了更大的倚仗。
这么柔弱的、痛苦的小孩,自然是英雄布鲁斯的拯救对象,换其他一些文艺明星,反而没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在来到费城拍摄前,奥斯蒙与其他演员有不少时间进行排练,希亚马兰也破天荒地尽可能以故事顺序拍摄,以便奥斯蒙更自然地体会科尔的心境。
通过色彩的应用,希亚马兰则为观众准备了一条线索,认知奥斯蒙与灵异的关系。
比如好几件红色服饰——分别属于不同的角色,角色穿上他们时,往往代表着科尔周围的灵异事件。
而贯穿的红色帐篷更是科尔的特异功能据点,这个最初带给他无尽恐惧的地方,也成了他直面恐惧的起点。
当然,这些红最终是为了影片最初的“红色把手”呼应,这是少数与马尔科姆连结在一块的“红”,当真相揭晓,暗示就成了最后的遮挡。
那间他永远都下不去的地下室,只有在他的“脑海”中才能抵达,即科尔所说的,鬼魂们只能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事。
除了红,一缕“白”也在灵异氛围营造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只是奥斯蒙要为此辛苦一些。
那会还不是CGI满地走的年代,而且希亚马兰认为特效不足以为他想象的情境提供足够真实的支持。
这就是人们呼吸冷空气时的“白气”。

此处我们就不费心科普白气是液态之类的了,总之奥斯蒙为了在镜头吐出这些“白气”,被围在一个类似“冰室”的环境中。
剧组会在近乎封闭的空间里打进冷气,而奥斯蒙在这些场景中往往穿的很少,自然的寒冷让他的身体反应非常真实,而越是真实就越是能展现灵异的效果。
因为在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妻子安娜也呼出了类似的“白气”。
只是科尔的白气意味着他注意到了鬼魂,安娜的白气意味着马尔科姆发现自己是鬼魂。
千头万绪都为最后一幕做伏笔。
前面提到,自从科尔说出“我能看到死人”,影片的“恐怖画面”就变得更多了。
不过,无论以今天还是往日的眼光,影片从来不以吓人为卖点。
对于我们东方观众,可能更容易与希亚马兰的重点产生共情,那是一种不舍人间,不舍近人,时有余恨的质朴情感。
这也是为什么希亚马兰为科尔准备的结局不是揭晓了马尔科姆的真相,不是扮演亚瑟王的回归青春,而是与母亲琳恩在车祸街道上的全面“理解”。
真正让他害怕的不是那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而是母亲因为这些看不见的惊恐与疏远。
马尔科姆一直在努力打破与科尔的距离,而科尔,也一直在努力拉回与母亲的距离。
车内这场戏的奥斯蒙以极佳的克制映衬了托尼·科莱特的崩溃,作为祖母的“传声筒”,他的情绪终究隔了一层。
这时反而是一直压抑的母亲需要宣泄的时刻,不仅仅是为了祖母那句“是的,每一天”,也是为了借此破除的母子“心障”。
希亚马兰给每一个离开的,没有离开的人都提供了某种慰藉,这便是第六感背后,看似不动声色,却比一个精彩的反转,更神秘,更隽永的沉浸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