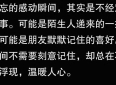从我记事开始,母亲的衣服口袋里面就时刻装着一块素淡的方形手帕,手帕上面绣着粉色的桃花、碧绿的垂柳和栩栩如生的春燕,无论下地干活、走亲访友,抑或赶集买卖,手帕都是母亲随身携带之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素朴穷瘠的乡下,母亲属于生活精致的女人,哪怕身上的衣衫业已洗得发白褪色,她也会竭力保持一尘不染,尤其是面部和双手,更是难觅丝毫灰尘。而对卫生起到关键作用的,便是那块方形手帕。
小的时候,我经常被母亲打扮一新后带去十里八乡走亲戚吃酒席。彼时吃席宛若过年,大人品尝山珍海味尚且顾及体面,而小孩看到肉食就像馋猫邂逅鲜鱼一般,顾不得多少礼节便开始大快朵颐起来,常常一道荤菜上桌,餐盘即刻见底。母亲吃席颇为讲究,她会把鸡腿或者剔过骨刺的鱼肉夹到我面前的碗里让我尽情享用。而她自己在不疾不徐地吃席的同时,还会不时地从口袋里面掏出手帕,给我擦去嘴上的油渍。母亲用她力所能及的方式,保持着一个乡下女人的优雅和一个顽劣孩童的干净。一场宴席吃下来,满桌食客早已成了手脸沾满油污的花猫,唯独我与母亲,在那块手帕的保护下,依然保持着清爽洁净的体面。
手帕的作用并非囿于酒宴之上,更多的时候,它还是我们下地干活时的“擦汗神器”,是不慎受伤时用于自救的“医疗器具”。有一回,母亲正在麦地里拔草,我则拿着镰刀在麦地地头割猪草,由于天干地硬草浅刀锐,我使用镰刀去砍地上的野草时,弹力作用致使锋利的刀口直接砍在我的左手中指之上,霎时之间,鲜血汩汩而出。我忍着疼痛向母亲求救,闻讯后的母亲放下手里的活计就奔到地头,并顺手拔掉几片刺刺芽叶放于掌心揉碎后敷在我的伤口处,然后有条不紊地掏出手帕给我包扎伤口,伤口刚刚包扎好,那块素雅的手帕上很快就被鲜血染出了几朵红云。母亲抚摸着我的脸颊问我疼不疼?我委屈地摇摇头,哽咽着拥进她的怀里。母亲告诉我说,吃苦受累是乡下孩子常有的事,“泥孩子”没有“金贵命”,想要改变命运,只有发奋读书。我看着那块被鲜血染得越来越红的手帕,想着猪圈里面那几头嗷嗷待喂的黑猪,眼泪不禁簌簌而下。
母亲不仅自己随身携带手帕,就连父亲也不例外。父亲身为村落小学的民办教师和十里八乡的专业兽医,当属方圆十里有头有脸的名人。在母亲的悉心照顾和耳濡目染下,父亲几近脱离了农民的“本色”,他常穿一身笔挺干净的海军蓝的衣裳,褂子左上方的口袋里面插着两支英雄牌钢笔,右下方的口袋里面则装着一块天蓝色格子条纹的手帕。并非父亲标新立异追求另类,而是在那个年代,不管男女,钢笔与手帕,是文化与文明的象征,是品位与精致生活的标配。手帕于父亲而言,最大的功能就是擦汗,以时刻保持面容整洁。他和母亲一样,每次用完手帕都会板板正正地叠好后再放到口袋里去,以备不时之需。
我读小学以后,母亲也给我买了一块宝蓝色的条纹手帕。我学着父母的样子,把手帕叠得方方正正,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口袋里,适时用它去污保洁,并借助手帕的“净化”与“美化”,尽力让自己成为像母亲一样干净整洁的人。然而愿望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我天生淘气,常常一天下来,手帕就被用得脏污不堪。对此,母亲非但不会责怪于我,反而还会对我提出表扬,说手帕越脏说明使用的频率越高,只有经常使用手帕的人才更讲卫生。
后来,母亲又给我们一家三口各自买了一块新的手帕,旧手帕与新手帕日复一日交替使用,保证了卫生的延续性,而洗手帕也成了母亲雷打不动的生活日常。我每次站在阳光下看着晾衣绳上那几块迎风招展、色彩迥异、散发着洗衣粉芳香的手帕,就会想起很多父母教导我讲卫生的故事。
那些关于手帕的温暖故事,是当下各类花样频出的一次性纸巾,所不曾拥有的感动。
责任编辑:谢宛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