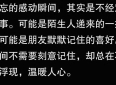母亲学问不高,也未必懂得多少做人之道,但她以一种朴素的判断来决定对孩子的要求标准,甚至不惜用强硬手段制止孩子们有损高尚品质的行径。
父亲给我起的名字不算好,因为拗口不好叫所以不好记,以至于我的名字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数百次,还是没有多少人记得,人们习惯喊我“实话实说”。
这便又多了层压力,实话实说就意味着不撤谎,可谁又没撤过谎呢。专家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从未撤过谎,那他就正在撤谎。
但“实话实说”成了你的别称,对你的要求就会与众不同,就像吃肉,本不是大事,可你一边做和尚一边吃肉就格外不行,这关乎职业道德。“实话实说”爱撤谎,非上小报头条不行。
人不是生来就会撒谎,该撒时就撒了,很有些无师自通的味道,但多少总会有些原因。先承认,我曾无数次撒谎,大部分撒完就忘,不记心上,只有几次是刻骨铭心的。
上小学四年级,一日下午上学路上。秋风拂起些灰尘,远远地,我们看见柏油路上有一团白,约摸有几十米远。几位同学一边走近。一边猜测是白纸、风筝、白布什么的。待真的走近,我眼尖手快,看清是纱巾,便捡了起来。那是一块很不错的纱巾,那个时代的奢侈品,它在几位同学手里传过后,重又传回我的手中。到了学校,我亲手交给老师,照例作为拾金不昧者而受到表扬。说实话,我那时是班级和学校都数得上的学生,受表扬乃家常便饭。这次表扬也就没放在心上,谁知竟埋下了祸根。
我傍晚放学,路上小玩一阵轻松走进家门时,发现母亲表情严肃坐在家中,似乎还沉思了许久。
对话大致如此:
“纱巾谁捡的?”
“我捡的。”
“当时有别人吗? ”
“有。”
“几个人? ”
“三个。”
“那怎么说是你捡的? ”
“我先看见的。”
“你撒谎! ”
我只记得母亲吼了这一句,便手执笤帚扑过来,劈头盖脸打起来。
我家兄妹四人,我最小。父亲是工程兵,逢山劈路,遇水搭桥,经常三过家门而不入,教养孩子的重任就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我们四人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说服教育虽可治本,但见效颇慢,母亲便常常急症下猛药,打为上策,意思是伤其筋骨以触之灵魂。
笤帚被打散了,母亲也歇歇手。顺便开始第二轮问询。
“为什么撒谎?”
……
“为什么说是自己捡的?”
……
“说! ”
“我觉得就是我捡的。”
“你觉得,别人都看不见,就你能看见,是吧?撒谎是品质问题,从小品质不好,长大就得蹲监狱,你知道吗? ”
“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撒谎? ”
“我没撒谎。”
……
于是,第二轮痛打开始了。
晚上,后背火辣辣的,我躺不得便趴着,趴着难以入睡便想:第一,以后遇到类似情况躲着;第二,查清谁告的密,断绝和他的一切关系。
印象中好像第二天我还发了高烧,记不清了,就算高烧也行。
母亲功劳很大,她学问不高,也未必懂得多少做人之道,但她以一种朴素的判断来决定对孩子的要求标准,甚至不惜用强硬手段制止孩子们有损高尚品质的行径。多少年以后,我和哥哥姐姐相继工作,得到的一致的评价是善良,老实,还有些窝囊。虽都默默无闻,无大成就,但兄弟姐妹间一直互相信任,互相关照,只一份融洽就让许多家庭羡慕不已。
转眼间升入初中,不知为什么,我特别迷电影。一次说晚上要上演朝鲜电影《火车司机的儿子》,我们在露天操场上摆好板凳占了地方。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电影就要开始,天降倾盆大雨,人们收起家伙四散回家,电影队也收起了机器。
我回家洗洗躺在床上,为没看到新片而懊丧,正欲昏昏睡去,雨过天晴。眼看星星月亮挂在天上,楚楚动人,我不由地想,会不会重挂银幕继续放映?于是我缠着母亲希望去探听一下。母亲虽百般阻拦,却经不住苦求,居然同意了。我几乎是飞到一千米以外的操场,果然不出所料,银幕已经又挂了起来。于是又“飞”回家中,一家人穿衣起床,欢天喜地去看新片。
了解了我对电影的挚爱,第二次撒谎便不足为奇了。
那天下午放学时,部队的地下车库正在联映老电影。同学提议进去看看。哪知一看,我的身子便像被磁石般吸住了一样。正在放映的是动画片《大闹天宫》,线条优美,人物生动,音乐动听,故事新奇,没有不看完的道理。紧接着演起了苏联电影《海底擒谍》,如果没记错,这是我第一次看间谍片,捏紧拳头,浑身热汗,早已忘了时间。第三部是国产电影《无名岛》,不容考虑,看罢片名我就挤出人群,边走边想用何借口搪塞过去,没有理由晚回家是母亲所不容忍的。
我可以告诉你,借口或者说谎言并不好编。
我也不想叙述母亲如何识破谎言并还以胜过上次的痛打。
你不要以为我的母亲是残暴的。用现今这个时代的教育观念去权衡那个时代的父母的做法是不公正的,我一直认定,母亲是善良正直的,一定程度上是伟大的。她的行为与做法也许并不高明,但绝对有她的道理。过程虽简单失之于粗暴,但初衷和结果都是好的。
高中二年级,已进入高考前夕的冲刺阶段(那时没有高三),我又一次因电影而撒谎。那天电影院上映新片《基督山恩仇记》,我刚刚读过大仲马的原着《基督山伯爵》,很为其中的爱情和阴森的孤岛监狱痴迷,班上几位文学青年亦有同感,于是相约逃课去看电影,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班主任李秉国把我叫出教室,手里拿了张电影票:“你去看电影吧,新片《基督山恩仇记》。”
“可还得上课呢! ”
“没关系,下午的历史课晚上回来我给你补。”
我拿着电影票茫然地转了两圈,决定回去上课并承认错误。
李老师说:“我知道了。人的一辈子分很多阶段,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重要的事,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参加高考。”
很多年后,我和李老师聊天说起这事,他说:“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
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