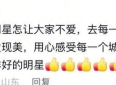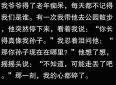哭过,泪是否太多,想闭上眼,却仍能看见,那淋湿的天。
大雨持续了十多天,疯狂的水,早已淹没了绵延的良田和若隐若现的屋檐,他的曾经,早在这场莫名的雨和力竭的呜咽中消失殆尽。他的脑海中,除了雨滴,便是回忆。
几天前,一场绵绵不绝的雨和一阵洪流,随之淹没了小村四周低洼的农田,将小村环成了孤岛。叫骂声,哭喊声,连成一片,这个他们曾经的乐园,如今却变了天。
绝望的人们都聚在一起啜泣,只是早已没有了力气。村长家的小院子也早已变得泥泞不堪,孩子们打着伞,抓捕小鱼虾,轻快的童年仿佛和洪水的忧愁无关。这场大洪水似乎想淹没他们这个平凡的世界。老村长大声地呵斥着众人:‘‘都别哭了,还嫌水不够深吗!’’
许多人就那么呆呆地抱着头,蹲坐在屋檐下,看着眼前那飞涌而下的瀑布和仍不间歇的雨柱,水在他们的世界里,从来没有让他们这般恐惧和无奈!
不知道是听了谁的提议,人们纷纷砍伐起树木。
村里的大树,早在两年前在一伙外地人的收购中贩卖殆尽。农村人喜欢扎堆,见不得小利益,又吃不得亏,于是乎村里人卖尽了在他们身边耸立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老树。如今,也只剩下玉良家门前的一颗老树,还孤零零的立在哪儿,像是在向人们诉说那最后的凄凉岁月。虽然曾经大伙心里都有些空落落的,但大多数人都认为那是值得的。可是现在,他们也只能把近两年栽种的小树砍来做成筏子这一条路了。
等待救援,简直是遥遥无期,小村早已隔断了所有与外界的联系。此时,他们是多么渴望能有一双翅膀,可即便是那样,在这大雨中,也只怕会被淋落吧。电话,在那个时候,对于他们这个山谷一角的人来说,是陌生的,也是神圣的。
老村长想把大家组织在一块造筏,可是众人都只顾着自家人的生死,谁还管的了那么许多。男人们疯狂地砍着树,编着绳,雨柱落在身上像刀割,只是他们早已麻木了。
刀,斧,锯;尼龙绳,麻绳,甚至连草绳都用上了,女人和孩子们也都在混乱的人群中忙碌着。老村长看着这一切,纵横的老泪再一次翻涌而出,只是人们都忙碌着,无暇顾及他的哀伤。他心里清楚,这样的情况,谁都很难走出这片天劫之地,他的泪,顺着雨水,流向了何方?
此时,玉良的父亲爬上了门前十几米高的老杨树,他带着铁锤铁钉,木板和家里所有的绳索。玉良知道,他这是要在树上给自己固定一个临时的落脚点。水,渐渐没过了脚掌,无论谁,踩出多么急促的脚印,也都不会有人看到了。然而,所有的人,都造好了一个简易的筏子,长的,短的,松散的,虽然不能确定,它们在这样的风雨中,能承受多久,可是大家都坚信自己能够活着走出去。
玉良看着站在水中的父母,他很茫然,却看见父母露出难得的微笑,笑的那么释然,那么沧桑。
他们催促着玉良爬上那颗老树,雨湿了他们的衣襟,也湿了他们的心。他们要用那未曾熄灭的心火,来为孩子照亮,为孩子取暖。
玉良哽咽着说:‘‘要走就一起走,要死就一起死!’’这个十岁大的孩子如此动情的话,也许让苍天听去了吧,于是,雨滴落的更加密集了。也许,那也是谁的眼泪吧!
玉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终究还是爬上了那颗树,他只知道,自己的视线,从未曾离开父母的容颜,那个画面,多少年以后,他依旧如此怀念。
父亲,母亲,他们还很年轻,和他们这个幸福的家庭,一切都将被无情的水,淹没!
他没有再哭,也许是泪尽了,也许是不想让父母淹没在自己的泪滴中。
父母没有做筏子,他们说既然跑不出去了,就应该让灵魂守住自己这一片小小的天地,而事实上,村子里能用得上的树早已被筏尽了。
树上有父母为玉良准备的干粮,还有用木板围成的简易小木棚,玉良躲在里面,分不清从湿漉漉的身上滴落的,到底是雨水,汗水,还是泪水!秋天的雨,一点也不比夏天雨季时来的小,唯一不同的没有了那么多的雷声和闪电。
玉良看着渐渐飘远的村里人和渐渐被淹没的自家小院,他胸口闷的喘不过气来。
父亲,母亲,为什么不爬上屋顶,为什么不和自己一起面对,这活下去的苦和累!
村里人都走了,带走了他们的钱和粮,也带走了他们的猪和羊,那不堪重负的小筏,在离村子不远处开始倾覆,散乱,最终被滚滚洪流冲尽了逃离的苦与忧。
玉良真切地看在眼里,那撕心裂肺的喊叫,早已化作低声呜咽,那些熟悉的人和事,都将淡去,淡去!
会有几个人能够活下来,玉良不敢想,可悲的是,那些丢掉性命的人,也将丢掉灵魂,玉良开始替父母感到庆幸,他紧紧地抱着那颗老树,他将和父母的灵魂缠绕在一起。
玉良又想起了父母最后跟他说过的一句话,如果能活下去,一定要再回到这个地方,他的家乡。他曾答应着点了头,泪水和雨水在那一瞬间也曾发颤。
此时,玉良又想起了老村长,他在哪里,他还活着吗?
玉良很努力地让自己想起更多的事,他知道他不能失去意志,他要坚持下去,他要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