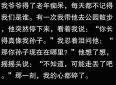19床病人住进产房的时候,妇产科特别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原来这是医科院配合医科大学传染病系的一个研究项目:艾滋病母亲分娩无感染婴儿。艾滋病人入住产房的消息顿时让妇产科炸了锅。开会时当着院长没人吭声,等会议结束,全体护士齐声抗议:“万一感染了谁负责?”连一些医生都嘟嘟囔囔:“要是污染了手术器械、床铺,造成其它病人的感染怎么办?”嘟囔归嘟囔,最后病人还是住进了妇产科病房,编号都是院长亲自挑的,特护病房,19床,说是图个吉利。护士长分配值班表,给这床分配人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去。最后,刚从卫校毕业3个月的我,战战兢兢走进了19床的病房。
戴口罩帽子穿长袖不说,我还特意得挑了一双最厚的乳胶手套。19床靠在床背上,腆着临产的肚子,微笑着看知我进来。我以为得这种病的女人多少要有点与众不同,一打量,发现她很普通,头发短短的,宽松的裙子,平底黑襟扣布鞋,脸颊上布满蝴蝶斑,一个标准的临产孕妇。
“你好。”她彬彬有礼。我心跳如雷,僵硬的笑了笑。第一天护理就要抽血,而血液又是艾滋病传播途径之一,想想都叫我头皮发麻。大概是太紧张了,一针下去没扎进静脉,反而把血管刺穿了。我手忙脚乱的拿玻璃管吸血,又找棉球,小心翼翼的不让血迹沾到自己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清理完毕,看看她的脸色,居然风平浪静。
“谢谢你。”声音温柔而恬静,标准的普通话显示出她良好的知识修养。回到办公室,我忍不住说:“哎,这个19床,怎么看也不像得那种病的人呀?”正在值班的李大夫抬头反问我:“那你认为得这种病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把我噎住了。李大夫把19床的病历递给我“看看吧。”翻开病历一看,19床运气真是不好,本来是一所大学的老师,年轻有为,30岁就升了副教授,前途一片光明,在去外地出差的路上遇到车祸,紧急输血时感染了HIV病毒,直到她怀孕做围产期保健检查时才发现。
从发现被感染的那一刻起,她的生命已被改写。可怜那个未出世的孩子,据说母亲感染艾滋病后生产的婴儿感染艾滋病的几率高达20%-40%,而且生产中的并发症和可能的感染对于免疫系统被破坏的母亲来说,常常是致命的。现在她一边待产,一边起诉了那家医院和当地的血站。估计能得到赔偿,可是有什么用呢?
19床的丈夫来的时候,妇产科又是一阵小小的轰动。一个艾滋病人的丈夫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怀着好奇心,装着查房,走进去。19床坐在床上,把腿搁在对面坐在椅子上的丈夫的身上,慢慢的梳头发,从头顶到发梢,安静悠然,丈夫帮妻子轻轻揉着因怀孕而肿胀的双脚。对妻子的怜爱从他的双手不可遏制的溢出来。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斑斑点点的定格在丈夫的手和妻子的脚上。这是,他们更像一对幸福的准父母。
“你觉得这孩子会像谁多点儿?”我整理着床铺,听着这一对夫妻细语呢喃,心里一阵难过,原本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啊。“我!”妻子娇憨地说。“皮肤不能像你吧?”丈夫呵呵的笑,“看你的小脸都成花斑豹了……”在眼泪出来之前,我急忙走出病房。
19床每天必须服用多种药物,控制HIV的数量,几乎每天都要抽血、输液。两条白皙丰满的手臂,从手背到胳膊,针眼密布。我手生,加上害怕,常常一阵扎不进,她却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只是很安静的看着我笑。护理了一个多星期,我渐渐的喜欢上她。
虽然“武装设施”还是必备的,但是给她扎针我非常认真,给药时也要重复几遍,直到她明白为止。有时候,我还会买几支新鲜的向日葵,插在花瓶里,放在她的床前。她的胎位一切正常,胎儿稍许偏大,头围接近了生产极限10公分。不过为了避免生产过程中感染,医生早就商定为剖宫分娩,连手术计划都拟好了,就等着产期的到来了。
虽然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多星期,但是31岁初产,又身患艾滋病,所以病房上下都高度戒备,随时准备进入接生状态。19床却很镇静,每天看书听音乐,还给未来的孩子写信,画一些素描,枕头下积攒了厚厚一叠。我问她为何坚持要这个孩子,她生育年龄偏大,又带病在身。她并不在意我的唐突,笑了笑道:“孩子已经来了呀,我不能剥夺他的生命。”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她抚摸着向日葵,半晌方道:“如果不试一试,孩子一点存活的几率都没有了。”
我的心情颇为沉重,病房出现死一般的寂静。我正要离开,她轻声唤住我:“我想拜托你一件事,万一生产时出了什么事,我先生一定会说保大人,可是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所以无论如可,孩子是第一位的。”
我眼泪不可抑制的流了出来,这就是母亲!
19床的手术已经安排就绪,是第二天上午,可是凌晨的时候,办公室里的紧急信号灯忽然闪烁起来,发出刺耳的警铃声,我猛地坐起来,一看牌号,“19床!”我一边招呼值班医生,一边飞速奔向19床的病房。惨白的日光灯下,19床的面色也是惨白惨白的。打开被子一看,羊水已经破了,更要命的是,羊水是红色的。
也就是说,子宫内膜非正常脱落,子宫内出血了。
19床脸上出现了第一次慌乱的神色。出血就意味着孩子遭受感染的可能会成倍增加。原本胎盘可以屏蔽过滤艾滋病毒,但是生产中的出血以及分泌物通常会使婴儿也被感染HIV。他疼得额头上全是汗水,仍咬牙强忍着配合手术前准备工作。
夜间担架一时没来,她二话没说下了床迈开步子就走。我搀扶着她,看着混着血污的羊水沿着她孕妇裙下肿胀的双腿留下来。她不管不顾,反而越走越快,仿佛她走快一秒,孩子得生的几率和不被感染的可能就增多一分。
当她躺在手术台上时,羊水已经成污浊色。这意味着胎儿处于危险的缺氧状态。麻醉师给她实行了硬膜麻醉,我开始拿探针测试她的清醒程度。
真要命,3分钟过去了,她依然清醒地睁着眼睛,说:“很疼。”
麻醉师汗如雨下,这种对麻醉药没有反映的体质他还是头一次碰到,但是胎儿的状况已经绝对不允许再加大麻醉剂量了。
她死死握住我的手,眼睛哀求的望着医生们,声音轻微而坚决:“救我的孩子!快救我的孩子!别管我!”
1分钟后,19床的手和脚被固定在产床上,麻醉师也预备好了针剂,主刀的李医生闭了闭眼睛,好似不忍心下手。
这是我做护士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号称“妇产科王牌”的医生脸上看到这样近乎绝望的神情。
手术刀迅速的在19床的对麻醉药不起反应的肚皮上划切下去,皮肤裂开,脂肪层、肌肉、黏膜、子宫……19床握着我的手骤然间收紧了,咬着毛巾的嘴里发出含糊不清、低哑却绝对撕心裂肺的吼叫声,身体在产床上剧烈的颤抖着……她的脸因疼痛而变形,我不忍目睹,眼泪成串的往下掉。
那是一种怎样的疼痛?
那是怎样的一种母爱?
终于,胎儿被取出来了,脐带绕在了颈部,因为缺氧,他的脸已经青紫。
几分钟后,她大汗淋漓的身体开始松弛,而这时,在李医生有节奏的拍动下,婴儿吐出了口中的污物,终于发出了第一声微弱但清晰的啼哭。
即将昏死过去的母亲似乎听到了这声音,努力地睁开眼睛朝孩子瞥了一眼,随后就沉沉的合上了。我为她解开固定的带子,发现她的手腕和脚腕处都已经磨出了血。而我的手,也像骨头断裂了一样,剧烈的疼痛着。
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一眼是19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那双恬静爱笑的眼睛合上之后,就再也没有睁开。
三天后,她就因为手术并发败血症,抗生素治疗无效,深度感染,永远离开了人间。值得庆幸的是,那孩子HIV测试为阴性。我们的医疗个案多了一个成功案例,听说市里的报社和电视台都要采访这个艾滋母亲成功分娩的健康婴儿。
我在清扫那间病房时,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了她留给孩子的信,还有图。最上面一页画着一个大大的太阳,太阳下一双小小的手。她给孩子写道:“宝宝,生命就是太阳,今天落下去,明天还会升起来。只是每天的太阳都会不同。”下面摆着一个漂亮娟秀的名字:“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