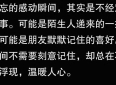都正年轻,她人长得靓丽,歌唱得也好,在剧团被称作金嗓子。他亦才华不俗,胡琴拉得出色,木偶戏的背景音乐,都是他创作的。偏偏他生来哑音,丰富的语言,都给了胡琴,给了他的手。
待一起久了,不知不觉情愫暗生。她常不吃早饭就来上班,他给她准备好包子,有时会换成烧饼。与剧场隔两条街道,有一家烧饼店,他早早去排队,买了,用一张牛皮纸包好,牛皮纸外面,再裹上毛巾。她吃时,烧饼还是热呼呼的。她给他做布鞋,从未动过针线的人,硬是在短短的一周内,给他做出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来。布鞋做成了,她的手指也变得伤痕累累,都是针戳的。
这样的爱,却不被世俗所容,人们都说,好好的一个女孩,怎么爱上一个哑巴呢?两人之间的关系肯定不正常。她的家人,反对得尤为激烈。最终,她妥协了,被迫匆匆嫁给另一个男人。
日子却不幸福。那男人脾气暴躁,贪酒,一喝多了就打她。她不反抗,默默忍受着。上班前,她对着一面镜子理一理散了的发,把脸上青肿的地方,拿胶布贴上。出门有人问及,她淡淡一笔,说不小心磕破皮了。贴的次数多了,大家都隐约知道内情,眼神里充满同情。她笑笑,装作不知。
他见不得她脸上贴着胶布。每次看到,浑身的肌肉会痉挛。他烦躁不安地在后台转啊转,指指自己的脸,再指指她的脸,意识是问:“疼吗?”她笑着摇摇头。等到舞台布置好了,回头却不见了他的人影。去寻,却发现他在剧场后的小院里,正对着院中的一棵树擂拳头,边擂边哭。
不是没有女孩子喜欢他,有个女孩常来看戏。她很中意那个女孩,认为很配他,有意撮合。他却不愿意。她急了,问:“这么好的女孩你不要,你要什么样的?”他定定地看着她。她脸红了佯装不懂,嘴里说: “我不再管你的事了。”
只要幕布拉开,他们便开始在小小的舞台后,用木偶人演绎着他们的爱情,那一刻,他们都觉得很幸福。然而,剧场却越来越冷清了,无人再来看木偶戏。出门,城中高楼一日多于一日,灯红酒绿的繁华,早已把曾经的“才子”与“佳人”淹没。后来,剧场承包给他人,剧团也维持不下去,解散了。
她回家了。彼时,她的男人也失业,整日窝在十来平方米的老式平房里,喝酒浇愁。不得已,她走上街头,在街上摆起小摊,做蒸饺卖。曾经的金嗓子,再也不唱歌了,只高声叫卖:蒸饺5分钱一个。
他背着胡琴,做了流浪艺人。偶尔回来,在街上遇见,他们怅怅对望,中间隔着一条岁月的河。
有时,他会把挣来的钱全部交给熟人,托他们去买她的蒸饺。他舍不得她整天站在街头,风吹日晒的。所以,总有一些日子,她的生意特别顺,总能早早收摊回家。他能帮她的,也只有这么多。
入冬了。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晚上,她在室内生了炭炉子取暖,男人照例喝闷酒,喝完躺倒就睡。她拥在被窝里织毛线,是外贸加工的,冬天,她靠这个养家糊口。不一会儿,她也昏昏沉沉睡着了。
早起的邻居来敲门,她在床上昏迷已多时,是煤气中毒了。送医院后,男人没抢救过来,她比男人好一些,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救,活过来了,人却痴了。
没有人肯接纳她,都当她是累赘。她只好回到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那里。老母亲哪里能照顾得了她?整日里对着她垂泪。
他突然回来了,风尘仆仆。五十多岁的人了,脸上身上,早已爬满岁月沧桑。他对她的老母亲写下一句话:把她交给我吧,我会照顾好她的。
他再没离开过她。他给她拉胡琴,都是她曾经喜欢听的曲子。小木桌上,他给她演木偶戏,他的手,已不复当年的灵活,但牵拉弹转中,还是当年好时光:悠扬的胡琴声响起,丝绒幕布缓缓拉开,才子佳人,湖畔相遇,眉眼盈盈。锦瑟年华,一段情缘,唱尽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