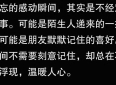那时,城市还没有醒来,路灯尚未熄灭,天上星星闪烁。男人却悄悄起床,去厨房,点起灶火。米是头天晚上就淘好的,加了山楂、大枣、白砂糖。淡蓝色的火焰越烧越旺,男人的瞳孔里,便也藏了一团小小的火焰。男人去洗手间,洗脸,刷牙,梳头,镜子里的男人,每天都在一点一点老去。男人再一次来到厨房,锅里的米粥已经沸腾,男人低了身子,他闻到了清香和甘甜。男人开始煎蛋,熟稔并极有节奏。男人手腕轻抖,蛋翻一个漂亮的跟头,香气更加浓郁。两只蛋煎好,男人开始切起咸菜。菜刀落得很轻,不仔细听,甚至寻不到一点声音。做完这些,男人进到卧室,对仍然熟睡的女人说,起床吧!这时候,距离男人的起床时间,恰好过去十五分钟。男人返回厨房,将米粥轻轻搅动,屋子里变得香气四溢。他往切好的咸菜上撒一点葱花,再淋上一点辣椒油———一切都随了女人的口味,男人可以将葱花和辣椒油精确到克。
两个人一边静静地吃饭,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早间新闻。收音机放在餐桌上,音量调到很小,他们不想扰到友好的邻居。这时候,城市仍然是安静的。
男人在阳台上目送女人离去,然后重回卧室。他很快睡去,甚至打起均匀并且响亮的鼾。他累,但他踏实。然后,闹钟突然响起,男人爬起来,天就亮了。男人匆匆出门,走到公交站点,等待一辆公共汽车。他本可以坐下一辆车,但他喜欢这辆,因为车上有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这辆公共汽车的司机。汽车远远地驶过来,男人就笑了。每天他为妻子做饭,每天妻子送他上班,两个人在车厢里相视而笑,谁也不肯说话。
女人工作的日子,男人必为女人早起十五分钟。
逢女人休息的日子,男人仍然会为女人早起十五分钟。不必调闹钟,无论头天晚上几点休息,男人总能将他的生物钟调到几乎分秒不差。他煎蛋熬粥,围裙将又胖又矮的他打扮成名店名厨。然后他唤女人起床,洗漱,吃饭,听收音机,再然后,不必上班的女人开始做家务,不必上班的男人坐在沙发上翻书,又突然看女人一眼,将书放下,为女人打起下手。
男人早起,只为女人能够多睡十五分钟。这样的日子过了二十五年,年年如此,天天如此。他和妻子一天天老去,没有老去的,是他们的相视而笑。仍然是初恋时的相视而笑,只在纯粹和羞涩里多出几分浓郁和相依为命。一个笑就足够了,他们能够读懂一切。
终于熬到退休的日子,女人的头上有了白发,男人的脸上堆满皱纹。晚饭时候,女人对男人说,每天十五分钟,二十五年,便是十三万分钟。男人低着头,问,这么多?女人说她刚刚算过,不会错。男人笑笑,不说话。女人说二十五年,你少睡了十三万分钟。男人再笑笑,不说话。女人说明天早晨,你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男人又笑笑,点点头。然第二天,当准时醒来的男人系着围裙走进厨房,当男人看到淡蓝色的火焰蹿起,他突然想起,这时候,他本该在梦里的。
转身,他看到,悄悄站在身后的女人,早已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