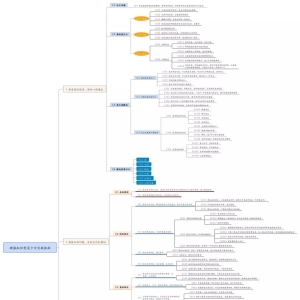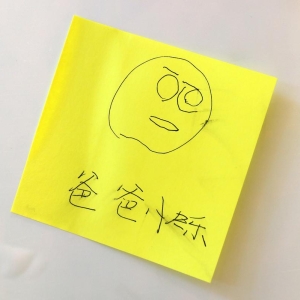真是人生悲喜一瞬问,像做梦一样。我在上小夜班,下午四点钟还得赶回来,翻开皮夹子,身上只剩三块七角钱,是半个月的夜餐补助费。第一次约会,总得请人家吃顿饭吧,粮票还有一斤,勉强凑合,可是这三块多钱够不够请一顿饭?

我惴惴不安地赶到东山车站时,队长已经到了,他给我们双方作了简单介绍,我才知道她姓许,叫许兰英,队长说:“你们好好谈谈,等吃你们的喜糖噢。”就走开了。
那天我们去了玄武湖公园,小许也放松了许多。她慢慢地靠近我,低低地问:“听说你是‘反革命’?”我点点头:“你怕吗?”她摇摇头,说:“我们村上的四类分子都是年纪大的,哪有你这么年轻的?‘文化大革命’揪出来的‘反革命’,我看都是假的。”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两个人的婚礼
我向她讲述我被定罪的缘由。她说她自己的历史:14岁就辍学上工,只读过初小二年缴。
那天,我送她一双青色的尼龙袜,她接过去用手摸了又摸,仔细叠好揣进包里。这就算我给她的定亲礼物吧。
下一个星期六,正好我转班,有一天的倒班休息,我们相约去见她母亲。
那天到小许家已经中午,她母亲忙着做饭招待我。饭后,老太问我多大了,家里还有什么人,为什么到农村来找对象。
我竹筒倒豆子般地讲了我的身世。
老太太认真听我讲完,叹了一几气说:“看来你也是个苦命孩子,我相信你讲的话,编也编不出这么圆。只要我女儿同意跟你谈,我没有意见,成不成就看你们的缘分。”(经典文章阅读 www.lingdz.com)
结婚那天,我还在上班。晚上,我俩在厂招待所里举行了婚礼仪式。桌子上点燃两支红蜡烛,我穿了一件干净的工作服。小许烧了两个菜,一碗萝卜烧肉,一盘红烧鱼。没有祝福的亲友,没有迎亲的伴娘,没有欢声笑语,没有喜庆的音响,静悄悄的新房里,就我俩端坐在那儿,相视无语泪两行……
我端起酒杯说:“对不起小许,我让你受委屈了,以后我有出头之日,一定会补场热热闹闹的婚礼。”
婚后,我们的家安在清沙嘴村半间草房里,尽管非常简陋,我总算有了一个可以牵挂的窝。
婚后第二年,我的“问题”得到甄别,被摘掉“现行反革命”的帽子。40年来,与结发妻子不离不弃,她那无声的背影,永久铭刻在我的心中。
编后语:当初一个最细微的体谅,就是一个最有力的支持和爱。这种爱怎能让人辜负,这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就是人性中最原始最淳朴的爱,这种爱值得我们温暖一生。